佛教道場往往對發心捐獻的信徒說:「功德無量!將來阿彌陀佛會保佑您。」對於前來貢獻勞力的義工,也總是說:「功德無量!將來阿彌陀佛會接引您。」凡是對佛教有貢獻的人,寺院的主事者經常都會說:「阿彌陀佛會添福賜慧。」每當聽到這種說法,我心就想:「信徒為佛教奉獻佈施,為什麼要麻煩阿彌陀佛來報恩?我們佛弟子又為佛教做了些什麼?信徒為佛教發心服務,為什麼要勞駕阿彌陀佛來感謝?我們怎能推諉責任,坐享其成?」
我一直覺得:我們不應該由阿彌陀佛代替我們報恩,而應該自我承擔這份感謝的責任。因此,凡是對佛門有貢獻的緇素大德,不一定對我個人很好,我都很樂意盡己所能來報答他們。像趙茂林居士不僅曾在佛寺、救濟院、大專院校佛學社團、廣播電台等處弘法,而且經常到各地監獄佈教,達二十年之久,我敬仰他這份度眾的熱忱,因此在佛光精舍留了一個房間給他養老,最後往生時,又將他的靈骨安厝在佛光山的萬壽堂。
張劍芬居士是三湘才子,經常應邀為佛教撰序作詩,擬寫碑文,然而到了年邁多病時,教界竟無人前往照顧致意,我知道以後,為他多次付費洗腎,希望能盡棉薄之力,代佛陀來感謝他畢生以文字般若弘法利生的貢獻。
戈本捷居士曾參加佛教譯經工作,並且幫忙編纂《佛光大辭典》。在他晚年時,我接他們伉儷二人同來佛光精舍居住,頤養天年。一九九一年,戈居士往生,我當時剛好骨折開刀出院不久,特地坐著輪椅前往靈堂為他拈香。他的夫人周法安女士感動之餘,匍匐叩謝。戈夫人說她是皇族後裔,只向天子、父母跪拜,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向外人行此大禮,我聽了覺得真是愧不敢當,因為我只是做佛陀的侍者,代為致意罷了。
孫張清揚居士是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對於佛教的貢獻更是至深且鉅。從東北到南方;從大陸到台灣;從搶救三寶到舍宅弘法;從慷慨出資,助興善導寺,到變賣手飾,引進大藏經;從成立書局,出版佛書,到行走各地,講經度眾……。對於台灣佛教今日的蓬勃發展,孫夫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滅的。然而自從孫立人將軍事件隱居之後,人情的澆薄現實令人唏噓,年老之後,更是無人問候。我有感於她一生衛教護法,功不可沒,因此經常去探望她,在她往生以後,雖知她有兒有女,但還是自願為其付喪葬費用,並且將她的靈骨送往佛光山安奉。
張少齊居士早年來台時,曾創設健康書局,出版佛教書籍,後來又成立琉璃印經室,影印大藏經,他的琉璃精舍,經常都有諸山長老海會聚集,商討教事。《覺世旬刊》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創辦的刊物,後來交由我接辦,至今已有四十餘年的歷史。張居士可說是台灣佛教文化的源頭耆宿,但到了晚年,卻門前冷落車馬稀。我向來十分感念他為佛教的種種辛勞,於是在美國為他找了一棟房舍以為安養之用。
我剛成立東方佛教學院時,曾聘請方倫居士為學生授課,但當他往生時,我卻為他張羅喪葬事宜;唐一玄居士也是那時的老師,後來他雖然到別處教書多年,我還是每個月定期將嚫錢送到他家。有些人問我:「他們已經離開佛光山多年了,為什麼你還一直如此予以厚待?」我覺得:他們除了教授佛子以外,著述也很豐富,我這樣做,無非是感戴他們為佛教作育英才及著書立說的貢獻,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在施恩於人,頂多是報恩感念而已。
年少時,每讀到《阿彌陀經》的迴向偈「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心中不免生大慚愧,虔誠誦經的功德殊勝,固然不容置疑,但是我們濫廁僧倫,為什麼要將報恩濟苦的責任推給阿彌陀佛呢?故當下立志傚法阿彌陀佛慈悲喜捨的精神,在娑婆世間散播歡喜、自在,為大地眾生佈施安穩、無畏。
太虛大師曾在文章中寫道:「……我母之母德罕儔……」我覺得這句話用來形容我的外婆是最恰當不過了。她一生行善助人,念佛不斷,慈愍有加。在我的記憶裡,她每天都到佛堂幫忙服務,從來沒有說過別人一句不好。當我在台灣聽到她逝世的消息時,真是悲痛逾恆,然而關山遠隔,且當時兩岸政策又不允許探親奔喪,故未能立即前往料理後事。盡管大家都說她的修行這麼好,一定會往生極樂世界,但我總覺得自己也必須略盡心意,所以後來在家鄉建了一座塔堂,安厝她的靈骨。
家師志開上人生前對佛教盡心盡力,犧牲奉獻,對我更有親賜法乳,長養慧命的恩德,我除了立誓以此身心奉塵剎之外,更為他修葺墓塔,奉養他現在的家人,以期能報厚恩於萬一。
至於生養我的母親,我雖然不能經常隨侍在旁,但我購買房舍解決她的居住問題,請人照料她的日常起居,我在生活上讓她不虞匱乏,在精神上讓她安樂自在……,她的一切需求,我都設法滿足,更重要的是,我廣度有情,視天下的眾生如父母,因此凡是她所到之處,普天下的信徒也都待她有如上賓。
雪煩、惠莊、合塵、真禪、圓湛等長老,過去與我有間接師生之緣,我不僅派人時予供養,數年前還親自接待他們到美國參觀。雖然自愧力有未逮,無法使其親炙彌陀,暢遊淨土,唯願盡己所能,先讓他們享受西方國家的文明設施。
四十年前,我還是一文不名的時候,承宜蘭雷音寺的妙專老尼師接納,讓我在那兒安住弘法;又蒙圓明寺的覺義老尼師提供安靜房舍給我專心寫作,讓我在那裡完成《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書,使我得償文字度眾的宿願。後來他們相繼年老過世,我為其重修寺院,再塑金身,使法脈永存,以為報答。
對於弟子們,我固然極盡教養之責,當他們的父母壽誕,我也敦促常住準備禮品禮金,讓他們帶回祝賀,聊表心意。每年節慶法會,佛光山都循例替生者消災祈福,替亡者誦經超度。此外,更定期舉辦「親屬會」,接待徒眾的家人來山一遊,享受「諸上善人共聚一處」的樂趣,凡是年老體衰,未能前來者,我也命有關單位親自送禮慰問。我衷心希望藉此微誠薄意,代替佛陀感謝這些「佛門親家」送兒女來山學佛修道,弘法度眾。
過去,經常看見同道規勸信眾趕快念佛,以求往生時極樂聖眾現前迎接。我那時常想:念佛雖好,極樂也妙,但為什麼不趕快解決他們現前的苦惱,讓他們先在心靈上找到一片淨土,在生活上得以少憂少惱呢?
所以當我開闢佛光山時,就決定要善加規劃,使信徒生亡都能在此安養,讓大家不僅在死後才能蒙受佛恩,即使在現世也能得到法益。
因此,在「接引大佛」邊設「萬壽園」,將墓地公園化;又建「萬壽堂」,供奉靈骨。週遭環境優美,前臨綠水,後靠青山,二六時中,梵音不斷,期使亡者都能在三寶的庇佑下,長眠於此。為使老病之人都能享受佛光照耀,我興建「佛光精舍」,安養耄耋老人;設置「安寧病房」,照顧臨終病患;辦理「佛光診所」,為人免費治療;成立「雲水醫院」,送醫藥到偏遠地方……。區區心意,只盼能為佛陀分擔些許憂勞。
剛來台灣時,有一位同道和我說:「大陸的寺宇氣派恢宏,比較能夠攝受人。」我乍聽之下,覺得那裡的道場不都一樣嗎?心中頗不以為然,但後來比較研究的結果,發覺的確有幾分道理。我想起經中敘述極樂世界黃金鋪地、七寶樓閣、八功德水、微風舒懷等情況,不禁對阿彌陀佛的善巧方便,敬佩萬分。所以後來自己建道場殿堂時,也非常注重式樣格局,總是力求外部的大方莊嚴,富麗堂皇,內部的美觀舒適,怡人心脾。雖然無法做到行樹羅網、水鳥說法的境地,但是我購苗植林,愛護禽獸,使來山遊客都能享受林園風光;我搬砂運土,移山倒水,建設淨土洞窟、佛教文物陳列館、展覽館,讓朝山信徒均能領略文化之美;我恪遵古制,取法現代,成立禪堂、念佛堂、禮懺堂,令佛子們都能在此獲得法喜禪悅;我用心擘劃一桌一凳、一瓦一石,希望凡是來這裡的一切眾生,均能滌盡塵慮,增長菩提。
在佛光山的大雄寶殿、大佛城等地方,我曾聽到弟子們對發心添油香的信徒說:「謝謝!阿彌陀佛會加被您的!」當下心裡十分納悶:「為什麼不請信徒先到客堂喝茶,到朝山會館吃飯,讓他們直接感受淨土之樂呢?」這兩個地方可說是佛光山最初的建築之一,目的就是方便信徒香客歇腳、用餐,雖說與西方淨土的思食食至相去甚遠,唯願一份美味的供養,能使大眾身心柔軟。近十年來,我們又興設信徒服務中心、麻竹園、檀信樓,派人為信眾服務,解答佛法問題,固然各種設施與彌陀世界的法音宣流比之,可說是望塵莫及,但盼一顆虔誠的心意,能讓大家般若心花朵朵開。
每到初一、十五,寺院中必誦〈寶鼎讚〉:「端為世界祈和平,地久天長;端為人民祝康樂,福壽綿長。」五十年前,我在叢林中參學時,經常反覆咀嚼這些辭句,當時的佛教寺院大都沿襲明清的山林模式,我深深覺得:愛國利民不是光用嘴唱,凡我佛子應該走入社會,以高超的教養來淨化人心,改善風氣,才能實際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所以,當我來到台灣以後,每到一地,我都極力宣揚佛法,白天講經,晚上寫作,有時還替人排難解紛,消弭怨懟。後來,更舉辦大型佛經講座及萬人法會活動,以使更多人均沾法益;同時又興設各種文教事業,期使法義能廣為流佈,影響深遠;成立各類慈善事業,希望鰥寡孤獨廢疾者不但皆有所養,同時能得到法水的撫慰。如今,各種佛光事業遍佈全球五大洲,希望對於當地社會安定能有稍許助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在台北聽說東京佛光協會會長西原佑一的父親往生,特地趕赴嘉義,為其拈香。西原會長把老先生的靈骨安厝在佛光山時,和我說道:「現在我先將父親送來此地,將來我們全家人都要到這個『佛光淨土』來。」這番話令我想起曾有一位信徒歡喜地向別人說:「我的娘家在台中,以前我常到東海道場禮佛,嫁到溫哥華以後,又經常去溫哥華講堂聽經聞法,沒想到現在移民澳洲,居然還可以看到佛光山的法師!我每去一處,都有佛光山的寺院能讓我念佛、念法、念僧,真是太幸福了!」當這些話輾轉傳入我的耳際時,心中不禁生起無限欣慰,雖然目前要做的事仍然很多,但是至少多年的願心已開始逐漸實現。
西方的極樂世界只有一個,並且必須廣修三福,念佛純熟,才能往生彼處,而人間淨土卻到處都有。只要我們有心,無論走到那裡,都能共沐在佛光之下,享受法水的潤澤。我們要將人間建設成佛光淨土,當世就能代替阿彌陀佛來報答眾生的恩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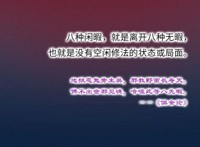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