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音義,是彙集解釋佛教經典中難讀難解的字音和字義的著述。它產生的來源有二:首先是為讀習佛典的需要。中國譯經,始於東漢,歷二百餘年迄劉宋時,即已卷帙浩繁,義理豐富。其間古代學者對於各別經典多有註釋,但對於一切經典文字的讀音解義,需有音義專著詳加註釋,方能使學人從音通義,明白了解經論內容。而音義書的出現。就是適應這種需要的。其次是外受小學家的影響。班固《漢書·藝文誌》,列小學凡十家,均屬於字書訓詁之類。漢、魏以來的小學家,有許多有關字學、訓詁、音韻之作,如孔安國、鄭玄的《尚書音》,孫炎、郭璞的《爾雅音》,孫登的《道德經音》等。這不能不給佛家著述以相當的影響。劉宋時,慧叡開始以經中諸字與眾音異旨為材料,著《十四音訓敘》。到了隋唐之際,佛典音義書籍就逐漸多起來了。
佛典音義,與一般書籍的音義一樣,有的僅注字音(如道慧《一切經音》,處觀《紹興重雕大藏音》三卷等),有的也兼釋字義(如玄應《一切經音義》等)。從內容方面來分,大致有三類:一、音譯部分的音義,二、義譯部分的音義,三、咒語證音。
音譯部分的音義,起源很早。東漢安世高、支婁迦讖、曇果、康孟詳諸人翻譯佛經時,對音譯梵語即加以註釋。其後,吳支謙、西晉竺法護、安法欽、法炬,東晉法顯,齊曇景,姚秦鳩摩羅什等新譯,也有音譯註釋。在這些音譯註釋基礎之上,乃有《道行品諸經梵音解》、《翻梵言》、《翻梵語》等書的出現。這些是早期的佛典音義作品,沒有音義之名,而且只限於音譯部分。其次是義譯部分的音義,這在音義書中佔的份量較多,因為在翻譯佛典的過程中,除了所謂「五不翻」必須用音譯而外,其餘大部分仍以義譯為主。最後是咒語證音,這部分雖不太多,而它的應用價值卻很大,可藉以研究各時代漢語字音,解決音韻學上的許多問題。
另外從音義和經典的關係來看,它的內容又可分為三種:一、一經部分的音義,如窺基撰《法華經為為章》等,二、一經全部的音義,如慧苑撰《新譯華嚴經音義》、淨昇撰《法華經大成音義》等,三、一切經音義,如玄應撰《一切經音義》,慧琳撰《一切經音義》等。
佛典音義,從體制上看,又可分為三種:一、隨函逐經註解的,如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雲勝撰《大藏經隨函索隱》(今佚)等。二、統一眾經分韻編類的,如行均撰《龍龕手鑒》等,三、統一眾經依文字部首編類的,如處觀撰《紹興重雕大藏音》等。
現存音義書中,以玄應與慧琳二家的著作最為重要。
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本名《大唐眾經音義》,道宣序及所譔《大唐內典錄》卷五,均用此名。其後《開元釋教錄》卷五著錄此書,改名《一切經音義》。其實此書所注經籍,僅四百四十餘種,未盡全藏。本書將藏經中難字錄出,為之註音釋義,廣引群籍,大都鑿然有據。但有不足之處,如莊炘謂玄應說字「以異文為正,俗書為古,泥後世之四聲,昧漢人之通借,其識僅與孔穎達、顏師古同科」。這些缺點,在其後慧琳書中,始大部分得到糾正。
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慧琳為不空三藏的弟子,於顯密教及印度聲明、中華音韻訓詁之學都相當通達。唐德宗貞元四年(788),他年五十二,開始撰《一切經音義》,至唐憲宗元和五年(810),歷二十三年撰成,書中所釋,悉為《開元釋教錄》入藏之籍。始於《大般若經》,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有玄應舊音可用者用舊音,餘則自撰。其釋音多據《韻英》、《考聲》、《切韻》等書,釋義多據《說文》、《字林》、《玉韻》、《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等書。其有諸書所不備者,則兼采儒經雜史百家之說。所引書籍,達二百四十餘種之多。本書音義精核詳審,前後諸家所作均不能出其右。除有助於讀經註經之外,凡研究儒經諸史疑義,求之於註疏而不得者,也往往可於本書采獲佐證。而且所引書傳皆隋末唐初之本,文字審正,可以校正今本偽脫之失。但本書也間有以古字誤為俗字的;有引《說文》竄改本的訛字而未能改正的,但不過是小疵而已。
佛典音義之較早出者有高齊釋道慧所譔《一切經音》若干卷,見《開元釋教錄》卷八(轉引自莊炘撰《唐一切經音義序》),但其書不傳。此外尚有云公撰《涅槃經音義》一卷。慧苑撰《新譯華嚴經音義》二卷。此外有窺基撰《法華經音訓》一卷,太原處士郭迻撰《新定一切經類音》八卷(見日僧智證《請來錄》,今佚),後周霅川西巒行瑫律師撰《大藏經音疏》五百卷(今佚)。後晉漢中沙門可洪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卷(《佛祖統紀》卷四十三稱可洪進《大藏音義》四百八十卷,誤)。遼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凡《開元錄》以後至《貞元錄》之間續翻經論及拾遺律傳等書二百二十六卷,本書都續注了音義)。其次有宋太祖乾德五年(967)釋雲勝(一作文勝)撰《大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今佚)。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釋惟淨等撰《新譯經音義》七十卷(見《景祐錄》卷十五,今佚)。南宋處觀撰《紹興大藏經音》三卷,清淨昇撰《法華經大成音義》一卷等。
佛典音義在學術研究上還有幾種作用,首先,如玄應《一切經音義》,所引群籍,關於儒經有鄭康成《尚書注》、《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夏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字書有《倉頡》、《三倉》,衛宏《古文》,葛洪《字苑》、《字林》、《聲類》,服虔《通俗文》、《說文音隱》及《漢石經》之屬,皆非世所經見。至於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證引經、史等古籍更多,且大部分均已遺佚,皆可供學者補輯逸書之用。其次,許氏《說文解字》,乃文字體制兼訓詁之書,在小學中非常重要。二千年來,展轉傳抄,其中偽脫、訛音、錯字、逸句等不一而足,琳、麟二家音義所引,大都可以補正,足供語文學者研究參考。又密咒一部分,因夙重音讀,它的翻譯與註音均經嚴格的選擇,而保存字音比較正確;另一方面梵文的音讀,雖經過長久時間而變化甚少,故以梵文原音為標準,刊定咒語的音譯,對考定譯音時代漢字的音讀提供了便利。凡此均可供音韻學家研究漢語古音參考之用。
一切經音義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唐釋慧琳撰。慧琳(737~820),唐京師西明寺僧,俗姓裴氏,疏勒國人,幼習儒學,出家後,師事不空三藏,對於印度聲明、中國訓詁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佛教音義一類的書籍,在以前雖有高齊釋道慧撰《一切經音》(若干卷),唐釋玄應撰《眾經音義》(二十五卷),雲公撰《涅槃經音義》(一卷),慧苑撰《新釋華嚴經音義》(二卷),窺基撰《法華經音訓》(一卷)等等,但有的只限於一經,有的且有訛誤。因在各家音義基礎之上,他更根據《韻英》、《考聲》、《切韻》等以釋音,根據《說文》、《字林》、《玉篇》、《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等以釋義,併兼采一般經史百家學說,以佛意為標準詳加考定,撰成《一切經音義》百卷。自唐德宗貞元四年(788)年五十二開始,至唐憲宗元和五年(810)止,中經二十三年方才完成。後十年,即元和十五年年八十四,卒於西明寺。
本書為經典文字音義的註釋之作。它將佛典中讀者與解義較難的字一一錄出,詳加音訓。並對新舊音譯的名詞,一一考正梵音。所釋以《開元釋教錄》入藏之籍為主,兼采西明寺所藏經,始於《大般若經》,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此據景審《一切經音義序》說,實際不足此數),約六十萬言,凡玄應、慧苑、雲公、基師等舊音可用者則用之,餘則自撰。其用舊音之處,也往往加以刪補改訂(其用雲公及基師音義,皆註明刪補,又引用《玄應音義》也多所改訂,如第九卷《放光般若經》卷一「緒,舊作辭呂反,今改用徐呂反」。「甫,舊作方宇反,今改用膚武反」。「俞,舊無反切,今補庾朱反」等等)。本書撰成後,於宣宗大中五年(851)奏請入藏。後經變亂,本書之存於京師者亡佚。後五代時契丹據燕雲十六州時,本書在契丹流行。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高麗國派人來吳越求本書不得。至遼聖宗統和五年(987),燕京沙門希麟繼玄應書,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就《開元錄》以後至《貞元錄》間,續翻經論及拾遺律傳等書,約二百二十六卷,為之註音解義)。後來遼道宗咸雍八年(1072),高麗國於遼得本書。元至元二十三年釋慶吉祥撰《法寶勘同總錄》,著錄此書,可見元時此書猶存,其後一度亡失。到光緒初年,我國復從日本得到此書,民國元年(1912)始由上海頻伽精舍印行。
本書內容精審,非前後諸家音義所能及。它在學術上的影響,有下列幾方面:首先,是對佛教義學的貢獻。佛典繙自梵文,無論是意譯或直譯,均難免有所訛略。且筆受者往往「妄益偏旁,率情用字」,而書寫者又隨便增減點畫,不但「真俗並失」,而且「句味兼差」。加以長期間展轉傳鈔,錯誤更多(如「羯鞞」寫作「鶡鷎」,「鞭[革+亢]」寫作「[革+亢]」,「厞礨」寫作「蓓蕾」、「莇」寫作「薅耡」,「庶幾」寫作「謶譏」,「狎習」寫作「謵」,「被褡」寫作「被闟」等等)。使人多有隔膜。慧琳註釋佛經,一本漢儒小學家以字音釋字義的原則,使人由普通義而明其理。這樣,開元入藏的佛經,由於此書之助,大都可以理解。
其次,是在文字學方面的貢獻。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一書,成為訓詁學的標準,惟傳本不一,經後人刊落,偽誤甚多。如用慧琳《音義》對勘,就知後人所刊《說文》中有逸字(如《說文》無「濤」字,而琳《音義》八十三卷,引《說文》云;「濤,潮水湧起也,從水壽聲」)、脫字(如《說文解字後敘》謂說解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胡秉虔氏撰《說文管見》謂說解止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字。據此則說解脫漏一萬零七百四十二字,而琳《音義》卷二與卷六《大般若經》癎字注引《說文》云:「風病也。」今說文即脫「風」字)、逸句(如本書卷十三與十四《大寶積經》及《集古今佛道論衡音義》,「桎梏」注引《說文》云:「桎足械也,所以質地也,梏手械也,所以告天也。」今《說文》逸「所以質地也,所以告天也」二句)、刪改句(如本書卷九十八《廣弘明集音義》,「瑤」注引《說文》云:「石之美者也」。徐《說文》改石為玉)、傳寫訛誤的字句(本書卷八十六與九十六《辯正論》及《廣弘明集音義》,甃注引《說文》云:「井甓也」。徐《說文》誤作璧),凡此均可以用慧琳《音義》增補訂正。可見此書在文字學上的價值。
復次,是在音韻學方面的貢獻。《說文解字》一書,素為研究古音者的準則。惟《說文》古音經南唐二徐刊定之後,被竄亂者不少,而慧琳《音義》所引《說文》,則能保存古音,可為研究古韻和音讀者之助。唐,宋韻書,多祖陸法言《切韻》一派,《切韻》為六朝舊音,保存於江左,因此唐人稱為吳音。另外還有元廷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一派為秦音。慧琳熟悉關中漢語,所以本書獨取元廷堅《韻英》一派的秦音(王國維據景審序,謂琳音音切依據元廷堅與張戩書,而本書注中卻指明專依廷堅的《韻英》),而不取陸法言一派的吳音,(如本書卷八檛打下注云:「下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今不取」。如本書卷首音《大唐三藏聖教序》復載二字云:「上敷務反,見《韻英》秦音也;諸字書皆敷救反,吳、楚之音也」。)可見一斑。後世,《切韻》一派的吳音盛行,而《韻英》一派的秦音衰歇,今可藉書上窺往古的關中音系。又本書卷五音玄奘譯《大般若經》第四百十五卷,四十三梵字,悉改舊文,謂奘譯為邊方不正之音,因此擯而不用。這是因為玄奘所學梵文為當時中天竺音系,慧琳所學則為北天竺音系(但慧琳自稱為中天音),故有參差,特加改易(慧琳書對舊翻陀羅尼有梵本可考者,都重新譯過。如《大般若經》護法陀羅尼,《十輪經》護國不退轉心大陀羅尼,《涅槃經》波旬獻佛陀羅尼等。又於《涅槃經》音義附辨悉談十八章)這也是對於梵文音韻研究方面可資之處。
本書在國內久已失傳,自清光緒初年復得之於日本,即為學術界所重視。一般學人對它的利用:一為輯佚,二為考史。因為本書所用材料,都是隋唐時代通行的古籍,而且徵引廣博,計經、史、小學書籍共達二百四十餘種。其中所收經部如鄭玄《周易注》、韓康伯《周易注》等,史部如宋忠《世本》、姚恭《年曆帝紀》等,小學部如李斯《蒼頡篇》、趙高《爰歷篇》、《文字典說》、《古今正字》等久已亡佚。所以自本書取回後,會稽陶方琦即利用它輯《蒼頡篇》以補孫星衍之不足。又續輯《字林》以補任大椿之不足。山陽顧震福利用它輯《蒼頡》、《三蒼》、《勸學篇》、《文字集略》四十六種,為《小學鉤沈續篇》(任大椿輯小學逸書二十四種名曰《小學鉤沈》)。此外如汪黎慶輯《字樣》、《開元文字音義》、《韻詮》、《韻英》四種為《小學叢殘》,易碩輯《淮南許注鉤沈》,十之八均取材於《慧琳音義》,十之一取材於希麟《續音義》,採用他書者不過十之一而已。本書還可用以考史。如敦煌發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首尾殘闕,不知何人所作。羅振玉據本書卷一百所標難字,考知為慧超所譔。近人陳援庵考《四庫提要》惠敏《高僧傳》之偽,利用本書卷八十六考知為慧皎書之前帙,等等皆是。另外本書還保存了一些佚書目錄,如《五天雅言》、《七曜天文經》、《西域誌》、《南海誌》、《崇正錄》、《釋門系錄》、《利涉論衡》、《道氤論衡》、《無行書》,稠禪師《宗法義論》等。
本書也有一些粗疏之處。即間有以古字誤為俗字的,有引《說文》竄改本的訛字而未能正其誤的,也有因失檢而自錯亂的(如浮字凡五見,卷七浮囊下注浮附五反,玉篇音扶尤反,陸法言音薄謀反,下二反皆吳楚之音,今並不取。然卷三浮囊下注浮,又用符尤反)。但這些只不過是小疵而已。
(田光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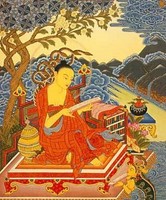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 證嚴法師
證嚴法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達照法師
達照法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靜波法師
靜波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