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述(一九三九年)
廿八年冬,外國人某氏至靈岩,謁見大師,有所請問,互用筆談,大師自述略歷行願如左。——編者志
經歷:光緒七年出家,八年受戒,十二年往北京紅螺山,十七年移住北京圓廣寺,十九年至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住閑寮,三十餘年不任事。至民十七年,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往香港。離普陀,暫住上海太平寺。十八年春,擬去,以印書事未果。十九年來蘇州報國寺閉關。廿六年十月避難來靈岩,已滿二年。現已朝不保夕,待死而已。此五十九年之經歷也。一生不與人結社會,即中國佛教會,亦無名字列入。
近來動靜:自到靈岩,任何名勝均不往游,以志期往生,不以名勝介意故。
行事:每日量己之力念佛,並持大悲咒,以為自利利他之據。一生不收一剃度徒弟,不接住一寺。
主義及念佛教義:對一切人,皆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為勸。無論出家在家,均以各盡各人職分為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人無貴賤,均以此告。命一切人先做世間賢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聖,往生西方。也並不與人說做不到之大話,任人謂己為百無一能之粥飯僧,此其大略也。
與蔡契誠居士書(一九二三年)
契誠慧鑒:先後天衰弱當以善於保養為事,若欲靠食物滋養,食素人宜多吃麥,食麥之力,大於米力,不止數倍。光吃了面食,則精神健壯,氣力充足,音聲高大,米則只可飽腹,無此效力。麥比參力尚高數倍,有錢人服參,乃是錢無處用,故作此消耗耳,非真能補人也。又大磨麻油亦補人,小磨麻油,以炒焦枯了,力道退半,人但知香,實則是焦味耳!蓮子、桂圓、紅棗、芡實、薏米,皆可滋補,豈必須血肉,方能滋補乎?總之,皆不如麥之力大,如不能吃,則兼帶著吃,久則自知,亦自好吃矣。吃雞卵之偈,乃妄人偽造,不可依從。保養之法,第一是寡慾,若不知好歹,任意嫖蕩,則死期將至,仙丹亦不靈矣!即不嫖蕩,自己室人亦須相與說其保身之由,暫斷房事一二年,否則或半年一相親,或一季一相親,倘日日行房事,則精髓枯竭,不死何能?節欲之人,所生子女,體壯少病,易於成人。多欲之人,或不能生,以精薄故,不能受孕;縱或生子,或即夭亡;即不夭亡,亦殘弱無所成就。汝不知已娶妻乎?若未娶,且緩娶;若已娶,決須暫勿同房,以期身體復元耳。此光切實為汝之言,汝能善體光意,自可福壽綿長,子孫發達矣。順候禪安。
蓮友印光合十 元月初六
其二
契誠慧鑒:接手書,備悉一切。現今之世,乃魔王外道出世之時,若宿世中未種真實善根,有信心者,盡入魔罥,以彼等群魔,皆有最希奇怪異之法子惑動人故也。江神童乃鬼神附體之能力,非真系生知之神童。前年友人張之銘以江神童《息戰書》見寄,命光看有不合宜者批之,當轉致。及光指其弊病,此友概不提及。甚麼宗教大同會,什麼釋迦化身,有智識者聞之,當直下知其為顯異惑眾之魔王,豈待問人!彼同善社老師,亦在四川,凡入會必須要出錢做功德,及出錢,則雲寄至四川,由老師調派。甚麼唐煥章,甚麼鄧紹雲,皆係妖魔鬼怪之流類,引一切善男信女,同陷邪見深坑。
佛法哪裡教人煉精氣神?無論甚麼外道,離煉精氣神,便無道可說矣。若是正人修之,亦可延年益壽;若了生死成佛,乃是說夢話。彼並不知如何是生死,如何是佛,胡說巴道一套,以騙人家男女。倘是邪淫之徒,則便借坎離交媾,嬰兒奼女交媾等名詞,誘諸少年婦女,悉為所污,且以此為傳道。而無智之人,雖受彼污,猶不以為非法,以其是傳道,不同無道之人夫婦行淫也。哀哉!世人何迷至此。靈學扶乩,乃靈鬼作用。亦有真仙降臨,乃百千回之一二。
其平常俱靈鬼冒名,斷不可以此為實,光《文鈔》亦略談之。江神童之道德會,亦扶乩,故與靈學會同一臭味,學佛人不應入此種會。而今之學佛人,有幾多依佛行,知佛法者?以故聞彼等之鬼怪奇特,遂如蟻聚烏合,蛤蟆逐鬧熱處跳了,可嘆孰甚!令友王君入魔已深,喻如狗子吃屎,謂無上美味。彼並不知佛,亦無正知正見,一向如狗子尋屎,蒼蠅逐臭,蟻子赴膻,名為學佛,實為學魔。今之出家者,有幾多知佛法者?每每亦學煉丹運氣扶乩等。指竅之說,最為惑人之本,若遇少年女子,多被此種法子所亂,罪大惡極。邪正不兩立,正法昌明,則邪法自可息滅,今魔種遍天下,亦眾生同分惡業之所感也。靜坐須提起精神,息心念佛,倘不提精神,一靜即睡著矣,此眾生通病。化修紫竹林大殿者,乃是吃喝嫖賭無資本,作此種事,借修佛殿為騙錢計,此阿鼻地獄之種子耳。
紫竹林大殿完完全全,要修做甚麼。汝且一心持戒念佛,任彼魔王外道,顯甚麼鬼本事,皆勿理會,則可不被魔徒牽入魔黨矣!六月後不可來信,以施省之發心修杭州梵天寺(系光勸發故必要光去),即蓮宗十一祖齊大師道場,須光去料理商量,不過一二十日;又要到南京法雲寺,梅蓀以法雲寺成立,必要光到方可,遲早隨光,往南京亦不過一二十日;由南京到揚州,以安頓《文鈔》事,《文鈔》將刻完矣,一出書,即又另排,已有數友任一萬部。大約九月半後,即可回到普陀,否則十月初必到,以天氣一冷,外邊不便故也。書此,順候禪安。
蓮友印光謹復 四月廿一日
復金振卿居士書(一九三○年)
智高居士鑒:人之入道,各有時節因緣,既因《文鈔》而知佛法,從事修持,即是皈依,不必又復行皈依禮方為皈依、不行皈依禮不名皈依也。但願汝能依到底,不中變,即真皈依,又何須每日頂禮於不慧也。果以禮不慧之禮以禮佛,則彼此均得巨益矣!
錫箔一事,雖非出佛經,其來源甚遠,古農雖不知來源,所說本於天理人情,何得又自作聰明,不以為是?光昔看《法苑珠林》,忘其在某卷,有二三頁說錫箔(此即金銀)及焚化衣物(此即布帛)等事,其文乃唐中書令岑文本記其師與一鬼官相問答等事,其人彷彿是眭仁茜,初不信佛及與鬼神,後由與此鬼官相契,遂相信,並令岑文本為之設食,遍供彼及諸隨從。眭問冥間與陽間何物可相通?彼雲金銀布帛可通,然真者不如假者。即令以錫箔貼於紙上,及以紙作綢緞等,便可作金及衣服用。此十餘年前看者,今不記其在何卷何篇;汝倘詳看,當可見之。其時在隋之初,以此時岑文本尚在讀書,至唐則為中書令矣。汝之性情,過於自是。古農所說,雖未知其出處,然於天理人情,頗相符合。
汝尚不以為然,便欲全國之人廢除此事,倘真提倡,或受鬼擊。世有愚人,不知以物表心,專以多燒為事,亦不可。當以法力心力加持,令其變少成多,以遍施自己宗親,與一切孤魂,則可;若供佛菩薩,則非所宜。然佛菩薩豈無所受用,尚需世人之供養乎?但世人若不以飲食香華等表其誠心,則將無以作感佛菩薩之誠。愚人無知,縱用此以供佛,於一念誠心上論,亦有功德,喻如小兒供佛以沙(阿育王前身事)尚得鐵輪王報。若愚人不知求生西方,用許多金錢,買錫箔燒之寄庫,實則癡心妄想。俗以自私自利之心,欲作永遠做鬼之計,恰逢不問是非,只期有佛事得經資之俗僧,便隨彼意行之,故破地獄、破血湖、還壽生者,實繁有徒。然君子思不出其位,但可以此理自守,及為明理之人陳說;若執固不化之人,亦不得攻擊,以致招人怨恨,則於己於人於法皆無利益也。
汝果真欲皈依,當以吾言為準。否則縱親來皈依,亦是有名無實,有何師弟之誼,與皈依之益乎?祈慧察。光老矣(今已七十有一矣),精神不給,不得常來信。
印光謹復 六月初四日
致龔宗元居士書(一九三一年)
宗元居士鑒:吾人從往劫來,固有種善根之時,但以未遇仗佛力即生了脫之法門,故致仍然在六道輪迴中,不能自出也。汝之幼時,隨母信佛,乃是天性,及後飽服韓歐之毒,則其惡習也。至於夢中所見之境,亦屬宿世善根所致,而迷之至深,故致一時尚難立即回頭也。此之關係,極險極險,若不自振,則長此迷昧,恐連佛名亦莫由聞矣。今既知之,當為努力。又淨土法門,與其他法門各別。他種法門,皆仗自力;唯此法門,全仗佛力。南方宗門頗多,切不可參入宗門,圖得禪淨雙修之嘉名。宗門總以看念佛的是誰為開悟之一著,而絕不講信願求生,勿道不悟,即看得到念佛的本來人的面目,只算得是悟,去了生死,尚大遠在,若不到業盡情空地位,決定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不注重信願求生西方,則與佛相背,不能仗佛力了生死,以念佛人帶著宗門氣息,則得利益處少,失利益處多也。教則更為難以得力。而密宗語氣甚大,危險之極。汝且專注於信願念佛一門,而輔之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此自行,復以化他,則可決定住生矣!又凡居心動念行事,須以真實不虛為主,庶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矣!餘詳文鈔嘉言錄,此不備書。光老矣!無力應酬,祈勿常來信,唯慧察是幸!
印光謹復 六月二十日
復邵慧圓居士書(一九三二年)
慧圓居士鑒:手書備悉,昨明道師往申,令匯汝一百六十圓,以了汝事。汝雖與光相識多年,究不知光為何如人,今故不得不與汝略說之。光乃犯二絕之苦惱子。二絕者,在家為人子絕嗣,出家為人徒亦絕嗣。言苦惱者,光本生處,諸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闢佛之說,群盲奉為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餘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為法(光未從師,始終由兄教之)。先數年,吾兄在長安,不得其便;光緒七年,吾兄在家,光在長安(家去長安四百二十里),遂於南五台山出家。先師意光總有蓄積,雲出家則可,衣服須自備,只與光一件大衫,一雙鞋,不過住房吃飯不要錢耳(此地苦寒,燒飯種種皆親任)。後未三月,吾兄來找,必欲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則可。光知其是騙,然義不容不歸,一路所說,通是假話。吾母倒也無可無不可。
次日,兄謂光曰:「誰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責!」光只好騙他,遂在家住八十餘日,不得機會。一日,吾大兄往探親,吾二哥在場中曬穀,須看守,恐遭雞踐。知機會到了,學堂佔一觀音課,云:「高明居祿位,籠鳥得逃生。」遂偷其僧衫(先是吾兄欲改其衫,光謂此萬不可改,彼若派人來,以原物還他則無事,否則恐要涉訟,則受累不小,故得存之),並二百錢而去。至吾師處,猶恐吾兄再來,不敢住,一宿即去。吾師只送一圓洋錢,時陝西人尚未見過,錢店不要;首飾店作銀子,換八百文,此光得之於師者。
至湖北蓮花寺,討一最苦之行單(打煤炭,燒四十多人之開水,日夜不斷,水須自挑,煤渣亦須自挑出,以尚未受戒,能令住,已算慈悲了)。次年四月,副寺回去,庫頭有病,和尚見光誠實,令照應庫房。銀錢帳算,和尚自了。光初出家,見「楊岐燈盞明千古,寶壽生薑辣萬年」之對,並《沙彌律》言,盜用常住財物之報,心甚凜凜。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氣味者,均不敢用口舔食,但以紙揩而已。「楊岐燈盞」者,楊岐方會禪師,在石霜圓會下作監院,夜間看經,自己另買油,不將常住油私用。
「寶壽生薑」者,洞山自寶禪師(寶壽乃其別號),在五祖師戒禪師會下作監院,五祖戒有寒病,當用生薑紅糖熬膏,以備常服,侍者往庫房求此二物,監院曰:「常住公物,何可私用,拿錢來買。」戒禪師即令持錢去買,且深契其人。後洞山住持缺人,有求戒禪師舉所知者,戒云:「買生薑漢可以。」《禪林寶訓》卷中,五十四五兩頁,有雪峰東山慧空禪師答餘才茂進京會試求腳夫人力書,大意謂:我雖為住持,仍是一個窮禪和。此腳夫為出於常住,為出於空?出於常住,即為偷盜常住;出於空,則空一無所有。況閣下進京求功名,不宜於三寶中求,以致彼此獲罪,即他寺有與者,亦應謝而莫取,方為前程之福耳。
近世俗僧,多以錢財用之於結交徒眾俗家。光一生不願結交,不收徒弟,不住寺廟。自光緒十九到普陀,作一吃飯之閑僧(三十餘年未任一職,只隨眾吃一飯)。印光二字,絕不書之於為人代勞之紙,故二十餘年,很安樂。後因高鶴年紿去數篇零稿,登《佛學叢報》,尚不用印光之名。至民三、五年後,被徐蔚如、周孟由打聽著,遂私為征搜,於京排印《文鈔》(民國七年)。從此日見函札,直是專為人忙矣!遂至有謬聽人言求皈依者,亦不過隨從彼之信心而已。富者,光亦不求彼出功德;貧者,光又何能大為周濟乎。光緒十二年進京,吾師亦無一文見賜;後以道業無進,故不敢奉書。至十七年圓寂,而諸師兄弟各行其志,故四十年來,於所出家之同門,無一字之信,與一文錢之物見寄。
至於吾家,則光緒十八年,有同鄉由京回家,敬奉一函,仰彼親身送去,否則無法可寄。此時未有郵局,而且不在大路(今雖有郵局,若無人承轉,亦無法可寄)。次年來南,消息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聞人言,遂來山相訪,始知家門已絕,而本家孫過繼(此事在光為幸,以後來無喪先人之德者;即有過繼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孫也),以故亦不與彼信。以民國來陝災最重,若與彼信,彼若來南,則將何以處?無地可安頓,令彼回去,須數十圓。彼之來去,了無所益,豈非反害於彼。故前年為郃陽賑災,只匯交縣,不敢言及吾鄉(吾村距縣四十多里);若言及,則害死許多人矣。今春真達師,因朱子橋(近二三年專辦陝賑)來申,與三四居士湊一千圓,祈子橋特派往賑吾本村,西村亦不在內,然數百家,千圓亦無甚大益,由此即有欲來南者。
一商人系吾宗外甥,與光函,雲有某某欲來南相訪者,作何回答?光謂汝若能照應,令其得好事,則甚好;否則極陳來去之苦並無益有損之害,庶不致於害死彼等也。此事真師一番好意,並未細想所以,兼又不與光說,及光知,事已成矣,無可挽回。聞數十年前,湖南一大封翁做壽,預宣每人給錢四百,時在冬閑之際,鄉人有數十里來領此錢者。彼管理者,不善設法,人聚幾萬,慢慢一個一個散,其在後者,以餓極,拚命向前擠,因擠而死者,二百餘人,尚有受傷者不知凡幾。府縣親自鎮壓,不許動,死者每人給二十四圓,棺材一隻,領尸而去。老封翁見大家通驚惶錯愕,問知,即嘆一口氣而死。不幾日,其子京官死於京中。是以無論何事,先須防其流弊。光豈無心於吾家吾村乎?以力不能及,故不開端為有益無損也。
靈岩先只上十人,大家以姚某之病,遂方便彼住於其中,此事豈可為例。彼寺年歲好,所收租金不上千,不好則又要減,此外一無進款。近三年,因有皈依徒知靈岩系真辦道,每有托其打念佛七者,稍為津貼,故住二三十人。然光絕不於靈岩有所求。靈岩寺諸師,每有供其父母牌位於念佛堂者,報國代光校書之德森師,並其友瞭然師(現亦在報國),均以孝思,各供其親之牌位於靈岩。光則絕不言及此事,光若言及,彼固歡喜之至,以光有此舉,即涉有攘功及自私之跡。況素未見面,只汝一信而皈依,即可在此養老乎?
如此,則凡皈依之苦人,皆求光養老,光手中若能出金錢谷米,則亦非不願,惜無此道力,何能行此大慈悲事乎。昔福建黃慧峰,每以詩相寄,稍有薄信,光為寄各書;彼復求皈依(與光年歲相等),後又要出家。光極陳在家修行之益,彼自詡為發菩提心,實則求清閑,為兒孫減養老費也,且其言決烈之極。光曰:我在人家寺裡住三十年,一身已覺多矣,況汝又來依我出家,汝決定要來,汝來我即下山。何以故?我自顧尚不暇,何能顧汝乎。從此永不來信矣。可知前之道心,是為子孫求利之心,非真有道心也。
汝人頗聰明,然亦有不以己心度他人之心之蔽。在己分則知其艱難,在人分則謂其容易。不知光比汝尚為苦惱,以後祈汝自量己力以做事,若再令光代出錢財,則萬難如命以償。何以故?光不止識汝一人,亦不止只汝一人有求於光也。倘止汝一人,數年來用三五百圓,亦不甚要緊。又有此處災賑,彼處善舉,又將何以應之?即如印書一事,亦不能任意令寄。彼原有章程,想已看過,若隨人意要者即寄,雖有數十萬家當,亦辦不到,況大家湊錢支持乎。如要,當按照本發請,此則可以滿願;如謂有益於人,即當如我所要為寄,則此事當即關閉矣。
《普陀誌》,從前系請一不知佛法不信佛者所修,而且為光亦作一傳以附之。光極斥其非,後以一二事,彼不依光,光遂完全辭之,不過問。及彼修好,交與法雨退居,放大半年,才求光鑒定,光以無暇,故遲幾年,故此書絕無光之名字。以彼所錄光之書併名者,通去之不存。其請人寫,排版刷印,不派普陀一文。彼山中請書者,按紙工價,每部六角,共印三千部。除任者一千多部外,只存千多部,光尚須送人,汝令寄數包來代送,其心甚好,但亦是未知其難。
祈以後常存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凡事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人之心,度己之心。則汝後來決定會做到光明輝煌,人神咸悅地位矣。不知此苦口之藥,以為然否?祈慧察。又教誨淺說之板,萬不可存弘化社,以此事不定一年兩年即關閉,無基金,無定款,時局不好,人不相助,則不關何能支持乎?佛學書局,交通寬,營業性質,能持久,交彼則於彼於汝均為有益也。
此書系廿一年壬申春,大師示復慧圓者。大師道行堅貞卓絕,令人佩服,五體投地。書中指示各節,力持大體,獨具隻眼,均足為世楷模。其針砭慧圓舉事不量力,待人不原恕,尤為言言藥石,字字珠璣。藏之秘篋,九年於茲。今大師已生西方,而慧圓奉行不力,不免故態復萌,瞻仰手澤,曷勝悲慟!爰為發表,以志吾過,且以紀大師誨人不倦之慈恩焉!
庚辰臘八 弟子邵慧圓謹志
復如岑師代友人問書(一九三四年)
如岑師鑒:座下所問,略為說之,不能暢敘。
(一)既有佛堂,何須在寮房供佛。今人多半是粗心浮氣,殿堂上尚肆無忌憚,正念誦禮拜時,尚敢出下氣,則寮房之放肆,更不堪言。若寮房供佛,當作大雄寶殿想,或可少招罪過,否則其功甚少,其過無量。每見高座法師,尚不以出下氣為罪,而於念誦時竟敢行之,況悠悠泛泛之學人乎。座下所說,乃於無可設法中與彼作一方便。當以在殿禮拜為免招罪過之第一法。
(二)觀想之法,亦非全靠外相。如以外相為事,則報化本是一體,又何有報化相礙之處?譬如人子見盛服之父母,與見常服之父母,並不作此是彼非,彼是此非之想。其人觀佛,作此種執相之見,若非自誇工夫,便是固執不通。此種人久久或致著魔,非真修行之士也。
(三)像之可以供可以存者,供之或存之;其不能供不能存者,焚化之。毀像焚經,罪極深重,此約可供可存者說。若不可供不可存者,亦執此義,則成褻瀆。譬如人子,於父母生時,必須設法令其安全;於父母亡後,必須設法為之埋藏。若不明理之愚人,見人埋藏父母,以為行孝,則將欲以活父母而埋藏之而盡孝;或見人供養父母以為孝,遂對已死之父母,仍依平日供養之儀供養之,二者皆非真孝也。
經像之不能讀不能供者,固當焚化之,然不可作平常字紙化,必須另設化器,嚴以防守,不令灰飛餘處。以其灰取而裝於極密緻之布袋中,又加以淨沙,或淨石,俾入水則沉,不致漂於兩岸。有過海者,到深處投之海中,或大江深處,則可;小溝小河,斷不可投。如是行者,是為如法。若不加沙石,決定漂至兩傍,仍成褻瀆,其罪非小,而穢石穢磚切不可用。
(四)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豈有不救苦厄之事;觀音菩薩隨機示導,豈有不接引生西之理。念佛人臨終,親見佛及聖眾親垂接引,何得此種死執著。果如是,則佛也不足為佛,菩薩也不足為菩薩矣。生西當以信願為本,若遇危險念觀音,有信願命終決定生西方;或只專一念彌陀,有苦厄亦必解脫。古書所載,難更僕數。今於塵勞中則事事圓通,於修持中則事事死執,不當圓通而妄圓通,不當執著而死執著,此苦海所以長淪,輪迴所以無息之所以也!作此見者,直同小兒,如是之人,何足與議。慧察是幸。
印光謹復 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
與鄔崇音居士書(一九三五年)
崇音居士慧鑒:前三日,接到《歧路指歸》二本,見後附之徽章,頗不謂然。民國二年,北京法源寺道階法師,做佛誕紀念會,以釋迦佛像為徽章,光絕不知其事。事後,道階來普陀,送光一徽章,光痛斥其褻瀆。至十二年,仍復如是。上海亦仿而行之,今居士亦仿而行之,作俑之罪,始於道階。道階尚能講經,而於恭敬尊重,完全不講,亦可嘆也。彼會中所來之一切人員,各須身佩一徽章,若佩之拜佛,亦不合宜;佩之拜人,則彼此折福。然現在由道階提倡,已成通規,光亦知此事不易收拾,然以居士過愛,不能不為一說耳。放生一事,即上海一處亦辦不了,何可大張全國之名?
全國人民通在水深火熱中,無法可救,而況全國放生會乎!光以勸人吃素為真放生。大場以前之放生,一住兵,則通為兵作食料,以後永無戰爭則可,否則又是為兵儲蓄食料耳。居士護生熱心,可謂第一,然須詳審情理,方可得其實益。諦閑法師,慕慈雲懺主之名,祈盧子嘉以西湖為放生池,大家都去放生,壞人偷捕,政府屢次要賣,諸居士幾次贖,用數千圓,猶令遷之他處。此之殷鑒尚不知,而徒張闊大之名乎?祈慧察。
印光謹復 乙亥五月十五日
致徐志一居士書(一九三七年)
慧章鑒:念佛之法,各隨機宜,不可執定。然於一切法中,擇其最要者,莫過於攝耳諦(詳審也)聽。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行住坐臥,均如是念,如是聽。大聲小聲,心中默念,均如是聽。默念時,心中猶有聲相,非無聲也。《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念佛時能攝耳諦聽,即都攝六根之法。以心念屬意根,口念屬舌根,耳聽則眼必不他視,鼻必不他嗅,身必不放逸懈怠,故名都攝六根。攝六根而念,則雜念漸息以至於無,故名淨念。淨念能常相繼不間斷,便可得念佛三昧。三摩地,即三昧之異名,吾人隨分隨力念,雖未能即得三昧,當與三昧相近。切不可看得容易,即欲速得,則或致起諸魔事。得念佛三昧者,現生已入聖位之人也,故須自量。隨息之法,在《淨土十要》第五,《寶王三昧論》第九「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門」,觀之自知,故不多說。
印光復 八月初六日
致張覺明女士書(一九三九年)
朝覺鑒:昨日將欲以信件付郵,靈岩當家來言,蓮宗十二祖像,祈張居士畫幾軸,不知有工夫否?若心緒紛煩,不能操筆,亦無礙。若尚能運從前之妙筆,先畫一軸,掛號寄來,再為斟酌其規則。其第二三等,即可照樣,用四尺宣紙,上書八句七言古體詩頌,前標祖師名,後標年時,另紙書,裱於上。頌名師名,均書於像下傍之下,庶不致招以凡夫之名,加於祖像之上之過。紙祈居士代買,以免寄時疊折。十二祖即世稱蓮宗九祖,於八祖蓮池大師下加蕅益為九祖,截流為十祖,以思齊賢九祖為十一祖,下又添徹悟禪師為十二祖。《佛祖道影》後附九祖像。唯蕅益、截流二師無像(今皆有矣),徹悟則有紅螺照像。竊以古代之像,皆後人意想畫之,其諸祖理宜無須,惟善導乃長鬚長髮,此恐意想,未見有提及留鬚髮事;亦有短短之須者。惟徹悟之須,清秀而長,若以佛制論,似乎不用須好;若依世諦,則亦無妨。唯善導之長鬚發為可疑耳。此且從緩待後再定。祈慧察示復為荷。
印光謹啟 己卯正月
其二
朝覺居士鑒:昨接手書,備悉一切。畫像之事,係靈岩當家擬畫蓮宗十二祖師之像,令光各作一六句讚,以備遇歸西日上供之用。又各作七言八句頌,擬書於像上,光以律詩太拘,妄效古體塞其責。彼本擬請居士畫一二幅,光謂彼逃難,寄居人家,恐不能畫,若能畫者,宜令一手畫之,方無體格不一之弊。今閱復書,當即作罷,隨當家請何人畫。此事在光本意,亦不甚讚成,何以故?南方潮濕,不十餘年,又須另裱,此之費用,為數不少。若供牌位,一二百年,亦仍完好。以彼事事要好,尚不惜屢屢求人也。在莊嚴道場,則似乎有益,當此局勢,亦或致招禍。事事考究,殊非所宜。祈將此事,置諸度外,一心念佛,以期實益。祈將二像掛號寄來。
印光啟 己卯二月十二日
致德森法師書(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德森法師鑒:凡上海所有之款,通歸印《文鈔》,不必一一報明。光大約不久了,故將已了者了之,不能了者亦了之。光死,決不與現在僧相同,瞎張羅,送訃文,開吊,求題跋,斂些大糞堆在頭上以為榮。以後即不死,外邊有信來,也不要寄信來。師願結緣,則隨意答覆,否則原書寄回。五台之信不寫了,法度尚不以為然,寫之亦只自討煩惱,任他明心見性去。《藥師經》今日為寄去。以後師當與彼商酌,光不問事了。光自民六年漸忙,忙得不了,只為別人忙,自己工夫荒廢了,倘蒙阿彌陀佛垂慈接引,千足萬足。至於作傳、作銘、讚、誄、聯者,教他們千萬不要斂大糞向光頭上堆,則受賜多矣。祈慧察。師幫光十九年辛苦,不勝感謝。
印光謹白
光死,亦不必來山,以免寒涼,又及。
其二
德師又鑒:此刻似不如清晨之疲怠,諒不至即死。然死固有所不免,當與熟悉者說。光死,仍照常為自己念佛,不須為光念。何以故?以尚不與自己念,即為光念,也不濟事。果真為自己念,不為光念,光反得大利益。是故無論何人何事,都要將有大利益的事認真做,則一切空套子、假面具,都成真實功德,真實人方是佛弟子。光見一大老死,一人作像讚,雲於穆大雄,出現世間。又一弟子,與其師玉嵀作傳,雲其行為與永明同,殆永明之後身乎。光批云:以凡濫聖,罪在不原,玉師雖好,何可作如此讚乎。玉師有知,當痛哭流涕矣!好好的佛法,就教好名而惡實的弄得糟透了。吾人不能矯正時弊,何敢跟到斂大糞的一班人湊熱鬧?以教一切人為自己多多的斂些,意欲流芳百世,而不知其實在遺臭萬年也。光無實德,若頌揚光,即是斂大糞向光頭上堆,祈與一切有緣者說之。
印光謹白
最後訓示
印光大師,於丁丑之冬,來靈岩避亂,方便掩關,不預外事。三年以來,法體康強,精神矍鑠。十月二十七日,示微疾,深以靈岩法席久懸為慮,乃於翌午,召集班首執事瞭然、亮普、敬人、惟性諸師等二十餘人,及在寺諸護法吳谷宜、彭孟庵、吳南浦、沈祥麟、楊欣蓮、張德林、薛明念、朱石僧諸居士等,齊至關房,開示靈岩沿革,囑以現在監院,兼代住持妙真師,真除主席,以護道場,而維久遠。略云:靈岩為古道場地,清咸豐十年,遭兵燹,焚燬殆盡。同治中,僧念誠,蒙彭剛直公護持,略蓋十餘間小屋。宣統三年,僧道明,因失衣妄打無辜,致犯眾怒,遂逃去。寺既無主,所有什物,一無存者,田地亦遺失不少。木瀆鄉紳嚴公良燦,啟請真達和尚住持,真公即令其徒明煦代理,先建鐘樓,自是遂漸興復,其詳見於《功德碑記》。至民國十五年,鄂亂事起,戒塵法師與學者南來,真公即以靈岩相委,永為十方專修淨業道場,用度不足概由真公貼給之。十七年,戒師因事赴滇,將院事托付慈舟法師,斯時妙真師,已由真達和尚延至本寺,任監院之職,輔佐慈師,辦理寺事。
慈師旋往鄂閩各地,弘法講經,即由妙師以監院資格兼代住持職務,秉承真老和尚之意,十餘年來,建造念佛堂、大廳、寮房、大雄殿、彌勒閣等全部房屋,整理諸務,有興無替,實為諸班首執事、護法居士等所共見。現因報國寺改為靈岩山下院事,與清禪師發生糾紛,此事原系出自真老本意,由光證明。而蘇州諸山不明事實,誤聽一面之辭,致書於光,指妙師假光名義侵佔報國寺,實與事實不符。光生平不接一地方,不收一徒弟,人所共知,豈有要一區區報國寺之理?而彼等尚不知江蘇全省寺廟,賴光得以保存於前也,茲為諸公述之。先是民國十一年間,光在普陀之時,有定海縣知事陶在東居士,寄來報紙一張,內載袁某具呈江蘇省長,請以全省寺廟財產興辦教育,經省長王鐵珊(瑚)核准。其批示中,有「無戾於法,實衷諸情,審慎周妥,良堪欽佩,著教育廳令行各縣遵照辦理」等語。陶居士函云:「此隔江風雨,頃刻即至,師若不設法救濟,一省如是,他省傚尤,佛法前途,不堪設想。」
光乃致函南京魏梅蓀、王幼農諸居士,請向省府疏通,收回成命。時省長已易韓公紫石,韓云:省方既已通令辦理,未易取消,若欲挽回,須由彼等(指諸方長老而言)具陳理由,請求省方再予核辦。時妙蓮和尚,因魏、王之囑,念光遠居普陀,為江蘇寺廟,不避忌諱,竭力營救,故對具呈省方事,奔走諸方,勸請列名,幾經波折,不辭艱阻,奔走跋涉。加以其時泰縣有數處小廟,已為官廳沒收,將及於光孝寺,故僧眾群起恐慌,乃由光孝和尚邀同寂山和尚等三十餘人,集省請願,始與妙蓮和尚合作辦理,並淨老和尚領銜,具呈省署,幸蒙批准,其事始寢。事實俱在,俱可復按。若當年沒收寺產,見諸實行,則江蘇寺廟恐無一存。蘇州諸山於光之保存寺廟一段事實,既未詳悉,於光之不接地方、不收徒弟之素志,更未明瞭,竟謂光要一報國寺,豈非不達事實之甚耶?
今報國寺事既告解決,靈岩主席久懸,亦為重要問題。溯自戒塵、慈舟兩師相繼去後,以迄於今,妙真師慘淡經營,致有今日,即由妙師真除住持一席,想真老和尚必能同意,諸師亦當無異議也云雲。時在室緇素一致讚成,咸無異言,事遂定。並擇十一月初一日,為接位之期,一切儀式概從簡略。老人並言:靈岩為十方淨土道場,傳賢不傳法。當即以此為嚆矢雲。
庚辰十月廿八日
弟子朱石僧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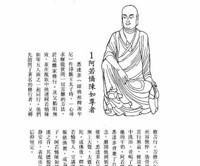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