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山棒,臨濟喝」,開創了禪宗宗師的「棒喝」教學法。臨濟義玄禪師是臨濟宗的祖師,他早年在黃檗禪師門下習禪,因此承襲了黃檗禪師嚴峻的禪風。印光大師雖是淨土宗祖師,但教界公認他通宗通教,「教理極深」(虛雲和尚語),「博通教義,兼達宗門,誠為一大通家」(太虛大師語),同時「品格高潔嚴厲」(弘一大師語)。
印光大師也常用呵斥的教學方式,使學人在聞喝的當下消除情見,提高覺悟,或斷疑生信,或樹立正知正見。所以,大醒法師讚歎說:「這真是古大德的風範。末世的佛門中又哪裡有這等大匠。」《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中說:「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即達官顯宦,絕無假借。」下舉敬舉幾例,以見大師棒喝教學法的風範。
清末翰林,江西彭澤許止淨居士,1922年前往普陀山,禮覲大師,以所譔的《禮觀音疏》進呈。(《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前,載疏全文。)內有「食廷璋之芋,剋日西行」句,老人便意其尚未斷葷。乃問,汝吃素否。答曰,吃花素。老人作色呵斥曰:「倒架子,如此大通家,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何能感化他人。」厲聲大吼,許居士欣然樂受。不但毫不介意,實在心悅誠服。次日上書請老人繼續編輯《淨土聖賢錄》,自願助成。於見面受呵之慈訓,表示萬分感激,嘆為名不虛傳。老人見其知見純正,文筆超妙,尤且虛懷若谷,殊為末世罕有,遂請編《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
竇存我居士回憶說:「大師自奉極簡。每飯只粗菜一碗。吃完以饅頭將菜碗擦淨食之。或以開水蕩洗飲之。在報國寺時。有一次因菜中用醬油稍好。將明道大師大加呵斥。責其虛消信施。言我等道力微薄。不足利人。即施主一粒米。亦無法消受。哪可更吃好菜。我們看見大師自律之嚴。自奉之儉。和虛己的慈懷。想著自己在家驕奢我慢的習氣。真是慚恨無地。我們侍坐於大師前。是一滴水也不許糟蹋的。我曾經將喝剩的半杯水。倒於痰盂中。大受喝斥。卻是奇怪。我從那次被喝斥後。才似見到佛菩薩超情離見之境界。才領解了佛法的真意。才覺得平日昏肆的罪惡。
那一次的呵斥。是與我以大利益。終身不忘的。哎。大師的精嚴。佛法的高深。是到了如何程度啊。」(竇存我《聞印光大師生西僭述鄙懷》)
大師歸依弟子王慧常(王柏齡將軍)1936年冬大吐血一次。他回憶說:「時人命何只在呼吸間。然省察自心。一不慌張。二不恐懼。但覺佛尚未念好為憾。愈後。與一緇友。朝江浙諸山。至蘇謁師。稟告病危時心理。師聞之。大喝曰。「汝若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什麼叫念好。十念當往生。」聆言之下。生大感泣。師破去我自障矣。由是常生自信。我決定往西方。我決不再分段生死。我已是西方人。爾後凡作事動念。均以西方人況比。彼土聖眾。有是行乎。有是念乎。不合者懺去。決不稍事容留。」(王慧常《追念我的師父印光大師》)
1922年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道尹黃涵之,匯印光大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齎送普陀,香花供養。德森法師自1926年起,在普陀隨侍大師座下。歷時已久,不知有政府贈匾額事,也未聽大師提到過。後來閱馬契西撰《印光大師傳》,才知道這件事。他問大師匾在哪裡?大師厲聲說:「悟尚未能,遑論圓明。瞎造謠言,增我慚愧。匾懸大殿,殊屬無謂。此空中樓閣,子何問為?」原來殿高匾小,德森法師經行其下,亦未瞻及也。
上述例子表明,大師具宗匠手眼,能準確察知弟子的根器和毛病而施以教誨。弟子再能虛心受教,師弟之間就機教相合,弟子深受其益。大師針對學人的毛病,痛下針錐。能接受,就進步。反之,若誤會,就會當面錯過善知識的教誨。如大師有一位弟子溫光熹在當時亂世之中想進入軍政界得一官職,以便給祖先修祠堂,遭到大師呵斥。溫居士未能領會,不得已,大師又給他開示:「光呵斥汝,乃是因汝不明而教導之,其言不切,則不能動汝之心。」
遇到善知識呵斥,我們應該記住大醒法師的話:「我幾次受到他老的棒喝。非常慶幸。假使在別一個青年學僧。也許要誤解受了印光大師的辱罵。可是親近大善知識(此係真實的大善知識。非徒有浮名者可比)。應生難遭遇之想。」(大醒《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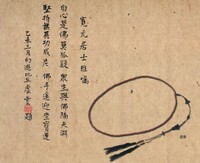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