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林禪寺在唐朝出過一個偉大的禪師——趙州從諗禪師,他的舍利塔現在還在這裡。趙州禪師有一個話頭,成為禪宗修行的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就叫「無門關」——現在我們的禪堂就叫「無門關」。
這個話頭來源於這樣一個公案:有人問他:「狗子還有佛性嗎?」趙州禪師說「無」。就是趙州禪師的這個「無」,成為一個話頭。這個話頭,從唐朝到宋朝、乃至到元朝,有很多禪人參究,也有很多人在這個「無」下明心見性。
「無」是什麼?宋朝有一位祖師叫無門慧開,專門講到無門關這個「無」,如果你在那裡參「無」,趙州禪師說「無」、「狗子無佛性」,若是觀想什麼都沒有,觀想「虛無」,那就錯了,那不是參禪,那是觀,有點像天台宗的空觀,所以「無」不是虛無的「無」。
「無」在這裡只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令我們起疑情,疑什麼?疑趙州禪師為什麼說無?就是疑這個。你也可能猜測,有很多推理,很多經典裡面的理解,現在告訴你,所有這些意識活動、猜測、理解、來自於經典裡的註解,在這裡都用不上,都不算數。你說我知道他為什麼說無,一二三四……打叉,不對!
告訴你,用意識在這條路上走,不可能找到答案,就算你以為找到了,它也不能解決生死輪迴的問題。既然解決不了生死輪迴的問題,它有什麼用呢?所以可以直白地說,你費盡心思猜測、理解,甚至找尋經典裡的註解,都白費功夫。
你說我參這個「無」,不知道從何下手,那就對了,參它就是要讓你感覺到不知從何下手;有的人參「無」,說心裡感到很悶,對了,就是要讓你感到悶;有的人說,我參「無」完全用不上功,對了,就是要那種完全用不上功,但又能不放棄,不斷地在心裡提起話頭,提起「無」的話頭。
在這種參究裡,支持我們不斷地提話頭的「什麼」,實際上是信。這裡的信有很多層:首先我們信趙州禪師,他說「無」,絕對不是隨便說的;
其次我們信自己的心,除了分別、妄想,除了理論、註解,無量劫以來我們生死輪迴就是靠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什麼呢?佛學裡有「識」,「分別心」,我們相信,我們的內心除了這個識以外,還有一條路。當我們不斷地提「無」的時候,實際上這個識的活動,會逐漸地削弱,妄想、分別會越來越少。
關於這個「無」,古人有很多比喻,這個「無」就像鐵釘,現在要你用嘴巴去嚼它,後果是什麼?後果可能是你的牙齒全部嚼爛掉,如果你堅持嚼的話。「無」就像一個鐵釘,在我們的心裡不斷地被咀嚼,就會把我們無量劫以來平時特別活躍的分別心那個牙齒嚼爛掉,讓它起不了作用。
它就是要讓你無路可走、無理可申、無話可說,把你堵在這裡,被堵在這裡,你還能不放棄,而且越悶、越堵,你越勇猛,越堅持,整個這個過程是一個鍛煉的過程。
這個鍛煉的過程,也許是痛苦的,剛開始也許是煩悶的、茫然無序的,但是就像嚼鐵釘,慢慢地你會從茫然無序、煩悶、沒有滋味中,嚼出一些滋味來。這個時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一灣水,很渾,有很多泥巴、雜質,這個話頭就像是往水裡扔一個東西,扔進去以後,在一個階段這個水會更渾,比以前還渾,比不參禪的時候妄想還要多。
但是越過這個階段之後,這個渾的東西就會沉澱下去,變清,清歸清,濁歸濁,清濁就分判了,到這個時候,你才覺得,啊!這裡面大有文章啊!你的心就不肯輕易放棄了。所以這個方法很絕,是要逼我們懸崖撒手,頭撞南牆,捨身跳黃河,逼拶我們。
因為所有的眾生都有一個習性,就是一定要在理路、意識上得到點什麼,所以眾生最大的貪在這裡。最大的貪不一定是貪吃、貪衣服,不是貪財、色、食、睡,我認為,眾生無量劫與生俱來的最大的貪是名。我講貪名的時候,你們想的是什麼?想當住持,大和尚,會長,這是一個很膚淺的理解。
名是名相。所有的名相是怎麼建立的?是由分別心建立的。所以眾生的分別心就像一個貪婪的野獸,要你不斷地給它餵食,餵什麼?它吃的那個食料是什麼?就是這些名啊!這個好,那個壞,就那些判斷。這個野獸在那裡張開血盆大口,要你不斷地餵這些名言、名相。
其實雲水行腳的師父的行腳體驗,對修行非常好,為什麼呢?因為他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特別能觀照心念。一個人到一個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寺院,我們馬上有一種本能的反應,要搞清楚這是什麼?那是什麼?這個人是什麼?這個是住持,這個是知客,這些反應來自於不安全感,不安穩,進而產生各種分別——名。
所以眾生最大的也是最難斷的貪,實際上是這個名,分別心這個野獸,現在我不給它喜歡吃的東西了,它不是喜歡吃山珍海味嗎?現在我扔給它磚頭瓦塊、木頭、鐵釘。我讓你吃!在我們不斷地扔磚頭、瓦塊、木頭的情況下,這個分別心野獸的胃口、貪就會歇下來。所以參話頭,我覺得是非常猛利的法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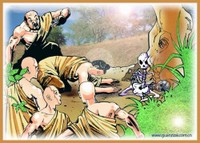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