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論》,一卷,馬鳴造,梁真諦譯。這是以如來藏為中心理論,為發起大乘信根而作的一部大乘佛法概要的論書。
此論的內容分為五分:一、因緣分,二、立義分,三、解釋分,四、修行信心分,五、勸修利益分。此中第一章因緣分,列舉製造此論有八種因緣,即是造論緣起。第二章立義分,顯示大乘的實質有二:一法,二義。法即是眾生心,心能攝一切法,有心真如相和心生滅因緣相;義有體大、相大、用大三大,這是諸佛菩薩所乘,故名大乘。第三章解釋分,根據立義分的法義,分三大段加以解釋:一、顯示正義,二、對治邪執,三、分別發趣道相。此中初段顯示正義,即顯示立義分所說的法義。先釋心真如門,顯示真如是一法界(即一切法)
的總相法門體,不生不滅,離言說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但依言說分別,有如實空和如實不空二義。次釋心生滅門,顯示一切法的體、相、用--即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它是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此識有覺和不覺二義;又覺中有本覺和始覺,始覺有不覺、相似覺、隨分覺、究竟覺四種差別。在不覺中,又有根本不覺和枝末不覺;由不覺故,生無明業相、能見相、境界相三種細相;又由境界緣故,生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系苦相六種粗相。其次說生滅因緣,眾生依心(阿黎耶識)、意(業識、轉識、現識、智識、相續識)、意識(分別事識)轉,一切諸法由此而生,唯心虛妄,由於不了達真如法界,念起無明,有六種染心。其次分別生滅相,說有粗細二種生滅,又有真如、無明、妄心、妄境界四種染、淨法薰習;由於此等薰習之力,而生流轉還滅之果。以上解說心生滅的法。此下顯示大乘自體、相、用三大的義:真如的體、相,不因凡聖而有增減,從本以來自性清淨、光明遍照、滿足一切功德,即是如來法身。真如的用是報、應二身:報身是菩薩所見,應身是凡夫二乘所見。最後顯示由生滅門入真如門的道理。第二段對治邪執,說一切邪執依於人、法二種我見,即凡夫五種人我見、二乘聲聞的法我見應加對治。第三段分別發趣道相,是說菩薩發心修行的過程,有信、解行、證三種發心,是信滿乃至十地菩薩發心修行之相。以上是本論解說大乘的部分。第四章修行信心分,是本論解說起信的部分。是就未入正定聚的眾生顯示修行而起信之相,要有信根本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四種信心,修施、修戒、修忍、修進、修止觀五種修行。另又為修大乘法心怯弱者顯示淨土法門,令專念佛往生淨土。第五章勸修利益分,敘說聞持此大乘法的利益功德。
在以上五分中,第一因緣分又為此論的序分,第二、三、四三分又為此論的正宗分,第五勸修利益分又為此論的流通分。或又以此論最初歸敬頌為序分,最後迴向頌為流通分,全論文五分為正宗分。
此論文義明整,解行兼重,古今佛教學人盛行傳誦。據傳當時真諦和他的弟子智愷都造有疏釋,隨後隋代曇延、慧遠也各造疏記,智顗、吉藏的著述中也引用此論文;唐代佛教界對於此論的傳習更廣,相傳玄奘在印度時曾談到此論的真如受薰之說,彼地學者聞之驚異。玄奘回國後,又將此論譯成梵文,傳往印度。而在中國由於賢首、天台二宗的興起,弘讚此論,智儼、法藏、元曉、澄觀、宗密各有疏記,湛然著作中也吸收了此論的思想。
因而此論入宋以來,流通更盛,一直到近世教、禪、淨各家,都以此論為入道的通途而重視它。
此論通傳是馬鳴菩薩造、真諦三藏譯,但在《馬鳴菩薩傳》和《付法藏因緣傳》中,都沒有馬鳴造《起信論》的記載。又此論所談如來藏緣起、阿黎耶識轉現等義,和馬鳴只說空、無我義(見《尼乾子問無我義經》等)也不相類,因而說是馬鳴菩薩造已屬可疑。至於此論的譯語,和真諦譯的《攝大乘論》、《金光明經》、《佛性論》等用語也頗不一致,而譯出的年月和地點,一說是梁太清三年(549)於富春陸元哲宅所出(見《歷代三寶紀》卷十一),一說是梁承聖三年(554)九月十日在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出(見智愷《起信論序》),一說是陳世初葉(557~569)譯出(見隋彥琮《眾經目錄》),也莫衷一是。隋法經的《眾經目錄》卷五則將此論列入疑惑部,認為"《大乘起信論》一卷,人云真諦譯,勘真諦錄無此論,故入疑"。唐均正的《四論玄義》卷十也說:"《起信論》一卷,或人云,馬鳴菩薩所造。北地諸論師雲,非馬鳴造論,昔日地論師造論,借菩薩名目之,故尋覓翻經論目錄無有也,未知定是否。"(此係日僧珍海《三論玄疏文義要》第二轉引,現存《四論玄義》無此文。)可見古來對此論的譔造和譯者已有疑問。
此論的異譯本,有唐實叉難陀譯的《大乘起信論》二卷,他的梵本來源有問題,據說是"于闐三藏法師實叉難陀齎梵文至此,又於西京慈恩塔內獲舊梵本"(見《新譯起信論序》)。其實當時印度已無此論,而此論梵本或系玄奘依據漢文還譯之本。如《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說:"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恩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後來此梵本在印度也不存在,因而也沒有藏文的譯本,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九說此論"蕃本闕"。
但此論在漢地佛教界甚為風行,如法藏、元曉、宗密、知禮都說此論通依諸大乘經,慧遠、智旭說此論是別依《楞伽經》而作,又因此論勸修淨土,因之唐、宋以來在漢地發展的賢首宗、天台宗、禪宗、淨土宗各派學人對於此論盛行弘講。而此論思想對於近世佛教學術界的影響也很大。關於此論的註疏等撰述甚多,現存的有梁代智愷(?)的《一心二門大意》一卷,隋代曇延的《論疏》二卷(現存上卷),慧遠的《義疏》二卷,法藏的《義記》五卷、《別記》一卷,宗密的《註疏》四卷,曇曠的《略述》二卷(敦煌寫本)、《廣釋》若干卷(同上),宋代子璿的《疏筆削記》二十卷、《科文》一卷,明代真界的《纂註》二卷,正遠的《捷要》二卷,德清的《直解》二卷、《略疏》四卷,通潤的《續疏》二卷,智旭的《裂綱疏》(釋新譯)六卷,清代續法的《疏筆削記會閱》十卷,民國梁啟超的《考證》一卷等。
此外,據《歷代三寶紀》卷十一說:真諦三藏於梁太清三年出有《起信論疏》二卷,這大概是傳說。其他的佚失的疏記,有梁代智愷的《論疏》一卷(?)、《論註》二卷(?、見《義天錄》),唐靈潤的《論疏》若干卷(見《續高僧傳》中《靈潤傳》),智儼的《義記》一卷,《疏》一卷,宗密的《一心修證始末圖》一卷,傳奧的《隨疏記》六卷(均見《義天錄》),慧明的《疏》三卷(見《東域傳燈錄》),宋代知禮的《融會章》一篇 (見《四明教行錄》),仁岳的《起信黎耶生法圖》一卷(見《佛祖統記》),延俊的《演奧鈔》十卷,元朗的《集釋鈔》六卷,智榮的《疏》一卷(均見《義天錄》)等。此論在朝鮮、日本流行亦廣。朝鮮古代僧人有關此論的著述,現存有元曉的《疏》二卷、《別記》二卷,大賢的《古跡記》(即《內義略探記》)
一卷,見登的《同異略集》二卷。此外已佚本還有元曉的《宗要》一卷、《大記》一卷、《料簡》一卷,憬興的《問答》一卷。
日本有關此論的章疏亦多,現存有湛睿的《決疑鈔》一卷、圓應的《五重科註》一卷、亮典的《青釋鈔》五卷、即中的《科解》二卷、貫空的《註疏講述》一卷、曇空的《要解》三卷、藤井玄珠的《校注》一卷、《講述》一卷、村上專精的《達意》一卷、《科註》一卷、湯次了榮的《新釋》一卷、望月信亨的《研究》一卷、《講述》一卷等。此外日本學者有關法藏的《義記》的註釋也多至數十種。
此論的日譯本,有島地大等譯、1921年東京刊行(收於《國譯大藏經》內)的一本,和望月信亨譯1932年東京刊行(收於《國譯一切經》內)的一本。還有鈴木大拙和李提摩太英譯本,前者曾於1900年在美國刊行,後者曾於1918年在上海刊行。
佛弟子文庫 > 中國佛教 > 正文
(?-805)唐代高僧,為淨土宗第五代祖師。縉雲(浙江)仙都山人,俗姓周。在睦州開淨土道場,集眾念佛。師每念佛...原指商賈買賣物品時之互相議價,於禪林中,引申為學人參禪辦道時之問答審議。如祖庭事苑卷一,謂審察量知佛祖之真意...即辨明一經之指歸。為天台智顗大師所立五重玄義之一。智顗為解釋諸經,而立有五種義解法,即釋名、辨體、明宗、論用...(雜名)謂印度之僧也。釋門正統四曰:漢武掘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朔。朔曰:可問西域胡道人。...攝取眾生之願。為三願之一。即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有關利益眾生之本願。又作攝生願、利眾生願。慧遠之無量壽經義疏...【六種無上】 p0299 瑜伽十四卷二十頁云:又有六法,於善說法毗奈耶中立為無上;不與一切諸外道共。謂見大師。聞正...子題:行前三心得有持義、識、想、受、行、犯一重戒餘戒常淨儼然、持毀皆有持義 戒本疏·持犯方軌:「前將止持,對...(術語)三毒中之二毒,貪慾與瞋恚也。釋門歸敬儀中曰:貪瞋一發,業構三塗。...可以修學佛道的根器。...(書名)又曰華嚴玄談。合清涼華嚴大疏中之懸談於演義鈔,為別行者,藏經目錄,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三十卷。...又稱外相。即外觀之相狀行儀。亦即表現於外在之行、住、坐、臥等四威儀。蓋無論男、女、出家、在家者,皆須注重身,...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宋西域三藏畺良耶舍(宋言時稱)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耶離國獼猴林中青蓮池精舍。與大比丘...十善業道經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奉 制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娑竭羅龍宮,與八千大比丘眾、三萬二千菩薩摩訶薩俱。...慈悲道場懺法傳 此懺者梁武帝為皇后郗氏所集也。郗氏崩後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 我們都知道,慈悲是佛教的根本,而因果律則是佛教理論的核心。《大智度論》中曰: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
我們都知道,慈悲是佛教的根本,而因果律則是佛教理論的核心。《大智度論》中曰: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 在整個藏教的《阿含經》,它在處理我們的生死業力這一塊,跟淨土宗非常類似,都是一種帶業往生的概念。就是業力我不...一個得道的高僧養了一條狗,名字就叫放下,每到給它餵食的時候,高僧就會站在廟門口,大聲呼喚放下,放下,放下!周...
在整個藏教的《阿含經》,它在處理我們的生死業力這一塊,跟淨土宗非常類似,都是一種帶業往生的概念。就是業力我不...一個得道的高僧養了一條狗,名字就叫放下,每到給它餵食的時候,高僧就會站在廟門口,大聲呼喚放下,放下,放下!周... 佛教興衰在人事的和合。在《涅槃經》上說:魔王要是看到有兩個普通的居士在鬥爭,他內心起歡喜心,但是這個歡喜的相...問: 弟子所在的縣,既無寺院又無居士團體,親人去世時,弟子如何助念?臨終如何勸導?在親人耳邊放念佛機可以嗎?...
佛教興衰在人事的和合。在《涅槃經》上說:魔王要是看到有兩個普通的居士在鬥爭,他內心起歡喜心,但是這個歡喜的相...問: 弟子所在的縣,既無寺院又無居士團體,親人去世時,弟子如何助念?臨終如何勸導?在親人耳邊放念佛機可以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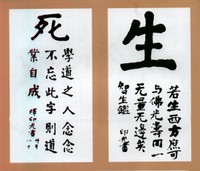 佛法真正學好了,就能夠用智慧觀照自己的身心狀態,時刻把握當下。有些人說:等我有空的時候再來學佛。仔細檢查一下...
佛法真正學好了,就能夠用智慧觀照自己的身心狀態,時刻把握當下。有些人說:等我有空的時候再來學佛。仔細檢查一下... 這個地方講到多欲為苦,就是講我們對慾望越執著,就會越痛苦。而且還有一點,就是當我們的慾望大於我們的能力的時候...
這個地方講到多欲為苦,就是講我們對慾望越執著,就會越痛苦。而且還有一點,就是當我們的慾望大於我們的能力的時候... 修行用功,固宜專精。然凡夫妄想紛飛,若不加經咒之助,或致悠忽懈怠。倘能如喪考妣,如救頭然之痛切。則於一行三昧...
修行用功,固宜專精。然凡夫妄想紛飛,若不加經咒之助,或致悠忽懈怠。倘能如喪考妣,如救頭然之痛切。則於一行三昧...
大乘起信論
【中國佛教】
| 上篇:大乘百法明門論 | 下篇:中論 |
(界名)受苦之眾生不堪阿鼻之苦而叫喚,故曰阿鼻喚。...
少康
商量
辨體
胡道人
攝眾生願
六種無上
持犯成就處所對心明止持
貪瞋
道器
華嚴懸談
外儀
【大藏經】佛說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大藏經】佛說十善業道經
【大藏經】慈悲道場懺法

好心真的能有好報嗎

業力要得果報,有兩個條件
放下心靈的包袱

成事不必在我,隨喜一切功德
大安法師:能用念佛機代替助念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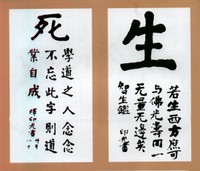
要從當下的一念去把握

【推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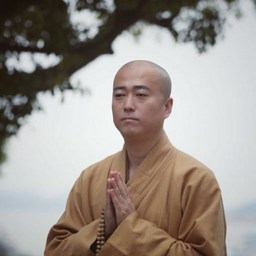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 證嚴法師
證嚴法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達照法師
達照法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