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人常說要修行,其實只不過是將修行當作‘懶惰’的代名詞而已!」
印順長老四十年前剛從香港來到台北時,曾經對我如足說,誠乃擲地有聲之高論,若非真正明師是無法講出這麼深刻的感言。這句話使我數十年來無時不警惕自己:我要做一個真正的修行人,可不能用修行作為懶惰的藉口。
記得有一回,道源法師在佛光山講授《大乘起信論》,課後我送他回寮休息。在路上,他忽然對我說:
「修行!修行!都快把佛教‘修’得沒有了!」
這種高瞻遠矚的見地,也只有心懷悲愍的菩薩才會因深思時弊,而有所發抒。
我曾多次周遊世界,看到一些先進的文明國家,他們國家大路旁的教堂林立,他們的博物館中都是宗教文物。如系信仰耶教,則全國人民強調他們是耶教的國家;如系信仰回教,則全國人民口口聲聲阿拉真主;而我們的國家,大都視宗教為餘物,我們佛教的主持者,並不鼓勵弘法利生,不重視世法欲樂,不講究犧牲奉獻,大都強調明哲保身,或入山修行,或自我關閉,致使佛法衰微,聖教不能深入社奮。人群,修持與生活脫節,真理與大眾遠離,讓邪魔外教到處橫行,讓迷信愚昧到處猖狂。孰令致之?誰能令之?怎麼不讓有心人唏噓慨嘆!
中國佛教自明清以降,因政治的迫 害,由社會走入山林,由資生轉為自修,遂一蹶不振,所幸今日由於教界大德之努力弘法與信眾的大力護持,佛教又有了一番繁盛的風貌。但有些人卻不明時務,妄學皮毛,或放著如來家業不去荷擔,整天高喊「修行」閉關,或棄置十方信施的慧命不顧,只在個人一修行一上著眼。他們無視福利社會的責任,乃至丟下世間上一切成就的好因、好緣、好事。試問倘若大家入山苦修,佛教的命運,蒼生的疾苦,將何以為度?
曾經有一位信徒這麼說:「師父!如果你們都去閉關,或入山修行,誰來接引我們,教化我們?」
誠然,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但修行絕非以遁世避俗來作為逃脫現實的藉口,也不能以此自我標榜,徒博虛名;更不可巧立名目,譁眾取寵。修行並非空洞虛無的口號,而應該是腳踏實地的自我健全,犧牲奉獻。
自慚我出家已有五十餘年,至今依然庸庸碌碌,慧解固然不足,修行也不算精進。不過,我這一生中確實不曾以修行作為懶惰的藉口,反而我發心服務,勤勞負責,從不好逸惡勞,敷衍塞責。
青少年時期,我在叢林參學,從棲霞律學院到寶華山學戒堂,從焦山佛翠院到金山天寧寺的禪堂,無論在律門、教門、宗門,我都刻苦砥礪,認真學習,隨眾上殿、出坡作務、春夏禪七、秋冬佛七,甚至行堂、典座、香燈、司水,更要上山砍柴,河邊擔水,我也都任勞任怨,全力以赴地為全寺數百人辛勤服務。寒來暑往,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十載星霜,就這樣一轉而過,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修行?總之,我都能直下承擔,法喜充滿地度過這段基礎的參學時期。
勞動筋骨的苦行實在微不足道,物質生活的艱難才足難以想像。當時中國社會歷經戰亂,百廢待興,民生困苦,我的常住由於僧多粥少,經濟更是拮据,因此三餐往往足以雜糧稀粥餬口,清湯淡水,或是夾著砂石鳥糞的豆腐渣、蛆蟲爬滿了的蘿蔔乾,經年累月少有油水下肚,遑論溫飽。衣服破了,只有用紙糊補:鞋底磨損,就以木片黏上:沒有襪子,便撿拾別人破舊不堪的棄襪穿上,聊勝於無,一切因陋就簡。多少年來,身無分文,寫了好幾封家書想跟母親報個平安,卻一直無法投遞,因為根本沒錢購買郵票,所以一封信今年寫了,放到明年,明年寫了,等到後年,遙遙無期,始終無法寄出。
物質缺乏的生活也還算是小事,在精神上,每天還要接受無理的要求、嚴厲的打罵、不盡的冤枉、無窮的委屈,甚至不准你抬頭多望世間一眼,不讓你對別人多說一句語言,受氣折磨,折磨受氣。盡管如此,我都能逆來順受,認為這是「當然」的教育,也是一個出家人「當然」的修行,故而能無怨無悔地完成修道基礎。
那時,我雖年輕,求證心卻非常殷切,希望能加緊修持,但是想到自己對人間毫無貢獻,對師門又無建樹,怎敢對常住有自私的妄求?怎敢遠離大眾而獨自修行?因此,只有在不礙工作,不為人知的情況下過午不食,刺血寫經,深夜禮佛,打坐參禪,偶爾也一年半載的禁語不言,或閉眼不看,或利用假期禁足,以埋首經藏……,凡此不一而足的密行體驗,雖然沒有令我豁然開悟,卻長養了我對佛法的信心道念。
不過,我要告訴今日的青年學子:我的學習修行,從來不敢離開僧團而尋求獨居:也從來不敢要求離群,自我任性:因為我覺得修行只是自己在生活中默默的密行,不值得標榜,不值得誇耀。如同一隻小鳥,羽毛未豐,離群以後,會不知道回來。教團的可貴,就是初學者的安樂窩啊!
一九四九年,初來台灣,身上一文不名,各處掛翠,備受奚落。為了感激中壢一家寺院留翠,遂從事拉車、買菜、打水、清廁、看守山林等卑微的工作,服務寺眾,以為圖報,繼而在南北各地奔波授課、弘法、譔文、寫書。一九六七年,我創立佛光山,度過與劉竹為伍,與洪水搏鬥的開山初期,並且在經濟困厄中籌建各種文教、慈善事業,期使佛法能普及社會。我不斷發菩提心,立堅固願,其中遭遇的困難與艱辛,在心中也覺得這是一個修行人應當如此的考驗。
一九八五年退居後,到美國閉關半年,以便讓後繼者能順利做事。出關以來,在課徒之餘,還經常應各地信眾的邀請,席不暇暖地在海內外奔波弘法,建寺安僧,更為信眾成立佛光會,期使佛法光大寰宇,庇佑全球。
回想我的一生就這樣無時無刻不在分秒必爭中度過,自愧未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但確知自己總是將我所了解的佛法行於日常,與生活相結合,例如:我不積聚錢財,而能喜捨結緣:我不向外妄求,而能承擔一切酸甜苦辣:我能甘於淡泊,在忙碌的行程中,以茶泡飯果腹充飢:我能隨遇而安,席地而睡:我能斗室讀書,車內寫作:我能與人為善,滿人希望:我能刻苦耐勞,不計毀譽;我能樂說不倦,給人歡喜:我能感恩惜福,不念舊惡:我能守時守信,不壞承諾:我能堅持理想,不畏難苟安……,我不高談修行,只一心一意,如理而行。
因此,我拜佛學佛,但我不希望成佛作祖;我佈施行善,但我不想上升天堂;我念佛行持,但我不欲往生蓮邦。我志不在了生脫死,我志只在多培養一些佛道資糧,我只願生生世世在人間,作一個具有平常心的和尚而已。
生死,豈是那麼容易了脫?沒有歷經千生萬死,不經三大阿僧祇劫,那裡能輕易地了生脫死?我之所以提倡人間佛教,乃遵照太虛大師「人成即佛成」的理想,實踐六祖「佛法不離世間覺」的主張。我們不需離世求道,在世俗人間,講經弘法是修行,服務大眾是修行,福國利民是修行,五戒十善是修行,正見正信是修行,結緣佈施是修行,慈悲喜捨是修行,四弘誓願是修行。人間的佛陀,不捨棄一個眾生;人間的佛教,不捨棄一點世法。我們認為:乃至行住坐臥,揚眉瞬目、舉心動念、示教利喜……,那一樣不是修行?為什麼捨棄人間佛教,要學習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家仙術,才叫做「修行」呢?
修行,修行,我們要靠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德行三具正的慈行三具正的福行、真正的智行,讓全法界一切眾生都能接受真正的修行,讓大家心中有佛法,生活有佛法,人人有佛法,普世都有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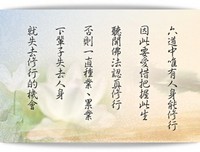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