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華寺繼任主持見月老人自述 弘一律師 批註 後學大光 校正
弘一律師題記
見月(注1)尊師,一生待人接物做事,態度威厲不露恩慈之情,也許有人會認為他過份嚴厲,不近人情。但是末法時代的一些善知識們,多半沒有錚錚剛骨,與世俗隨習同流合污,還自稱是「權巧方便,慈悲順俗,」來掩飾自己。這本書中所敘述的尊師的言行,正是對症的良藥。儒家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聽到管叔、伯夷兩人的人格風範之後,頑劣之人會變得清廉,胸無大志的懦夫都會樹起雄心大志)。我看這也適用於尊師見月。九月五日,我編寫完尊師年譜摘要,又校閱《一夢漫言》,增訂標要註釋,並寫了題記。九月十三日寫完《隨講別錄》兩篇,躺臥在床,追思見月老人的往事,併發願明年去華山(寶華山)禮拜尊師靈塔。不覺淚水漣漣,深感佛門氣象凋零不振,痛徹肺腑。
以前在藏經目錄中曾見載有《一夢漫言》。以為是現在人所寫的通俗勸導世人的佛書,就借了一本,讀了起來,才知是明朝寶華山見月律師自述他行腳參訪的苦行事蹟。我歡喜雀躍,深覺珍貴無比,反覆閱讀,連吃飯都忘了,閱讀之中,深受啟發,感動得潸然淚下幾十次。因而概括分段大意,加上眉註,並參照地圖另繪了一幀大師行腳路線圖(注2),以為後來研學此文的學人減少礙難。
甲戌八月十日閱讀完畢。二十五日抄錄完畢並此題記,弘一於晉水蘭若。
一夢漫言 卷上
康熙甲寅(公元2674年)冬,離言等各位阿闍黎(軌範師。意教授弟子,使之行為端正合宜,而自身又堪為弟子楷模之師。即導師),以及寺中眾班首領、執事,恭敬懇請,要我述說我的行腳參訪經過和事蹟,以資鼓勵後人。所以就提筆,從始至末,拉雜直述,不加文飾。
我是雲南楚雄府,許家之子。十四歲時,兩個弟弟尚小,不幸父母先後去世。兄弟三人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我伯父年事已高,膝下無子,對我們倍加愛憐,恩育教誨。當時我曾臨摩畫了一幅觀音大士像,人們都稱讚我是小吳道子。
我性好到處遊覽觀光,腳步不停。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十五歲時,聽說大理府和北勝州接壤之處,有一條金沙江,沿江居民以淘沙金生活。我就邀約了二三個同伴,走了五百里路去觀光,看到了實際情況,真是大地造化,養育生靈竟有如此方式。又聽說鶴慶府,地處群山之中,山勢如牆壁聳然而立,河流平壩道路險阻。古時有一業龍想把它變成海。此處東南地勢低凹,叫甸尾,水流到此,積聚受阻,漸將氾濫。有一印度神僧摩伽陀尊者,慈悲救生,用錫杖在甸尾的山腳處,穿鑿了數十個孔洞,深達五里多,把積水導入金沙江。在此我遇到了浪穹縣的學士肖暗初,他曾在楚雄請我為他畫一幅觀音大士像,一見面,很高興,就邀請去浪穹縣。接著又有孝廉楊紹先等人前來訪會。肖暗初和楊紹先兩家是親戚,都是巨富人家,各有名園別墅,大家情投意合,因此,我在那裡逗留了五年。
我二十七歲那年,正是崇禎元年。十二月初旬,正與諸位好友相聚於梅園遊玩。此園離浪穹縣城二十里,是肖暗初的書齋所在地,背靠石寶山,面積有十多畝,種了數百株梨樹,四季都可欣賞各種花卉。大家歡飲談笑,興頭正濃之時,我接到老家來信,告知伯父一直盼望我回去。他七十歲剛滿不久就去世了,未曾等到見我一面。當下我受到極大震驚,酒也醒了,傷心地哭了。我從來不信佛和道,這時突然發起出家的念頭,就對眾友說:「我實在不孝,父母和伯父之恩未報,大逆之罪難逃。現今決志出家懺罪報恩。從此一別,不復再聚。」大家聽後,都睜大了眼睛望著我,以為我發瘋了。
肖暗初說:「你一天都離不開酒,怎麼說起出家吃素的事。如果要出家,不必到別處去,我把這座園子奉送施捨給你修行。」楊紹先說:「肖兄既然奉施了園子,以後日用所需之物,一概由我包下,並把我隨身的家僮施捨給你聽便差使。」我說:「這四件事幸蒙二公成全,實屬多生良緣。我還要祈請你們今後葷酒不要再帶入此園。柴米就不限多少了。凡是行腳僧道,我都願供養齋飯。」他們都欣然答應下來,沒有絲毫礙難。
離此園二十里外有一座道觀,我前往拜訪,敘說了我想出家之事。該觀的一位老道士想誘說我做他的徒弟。我見他舉止沒有威儀規矩,談吐又不合情理,我就說讓我回去想一想再來回覆。我見他桌案上供著一部皇經,就想請回園中閱覽。他說:「你不是道士,怎麼能隨便說請經呢!」我當即脫下身上所穿之衣,和他換了道袍。他說:「既然你真出家,可以請去。」我回到了園裡將經卷供在案上,頂禮膜拜,自己改名為真元,號還極。
到了臘月三十日,我寫好一玉皇牌位供起來,至誠口稱神號進行禮拜。到了中夜,精神有點疲倦,不知不覺跪伏在地上睡著了。夢見萬里碧空如洗,一輪紅日高照。我來到一個大寺廟前,只見殿台高敞宏大,外有紅牆圍繞,松柏成行,中間有一門,看到有許多僧人在裡面,都是光頭,身披袈裟。我心生歡喜,想進去,但門檻太高,無法跨越。奮力試了幾次,忽然,就進去了。進去以後,覺得自己不是道士,而成了僧人模樣。見到眾僧圍繞之中有一高座,上坐二老僧,身著紅衣,笑嘻嘻地招手要我上去。我就擠開眾僧走上去。那位老僧拿了一卷經書給我,說:「你來給眾僧宣講。」我就接過來,站在座旁開講,眾僧都跪地而聽。
待到一覺醒來,渾身汗流,講的什麼內容也全忘記了。我就想,我終究不是道家門中之人,以後必定做佛門之僧。天明之時正是崇禎二年,我二十八歲。從此每天跪誦皇經一部,隔三日拜懺謝罪一週,每次作迴向祈禱時都悲咽涕泣,申白報恩。舊時的熟人好友來園隨喜,見我以前的俗氣全無,真實修行毫不懈怠,都發生信心,讚歎不已,有的發願,終身吃素,有的要脫塵出家。從此百里以內都知道肖家梅園有一位還極道人。
離浪穹縣城八十里,有個三營鎮,那裡有座大覺寺,定於崇禎三年春起建龍華法會。我就於元宵節前往隨喜,恰遇主僧雲關法師和籌建法會的各位會首在大殿裡。我肅整威儀禮佛之後,進了齋堂坐下。有一居士,白髮儒中,走上前來合掌致禮,問我從哪裡來。我說:「自浪穹來。」他問:「你會見過肖家梅園的還極道人嗎?他的道念和修行如何?」我說:「曾經見過面,此人只可聽聽名聲而已,不能見面,假裝修行,實在是炫耀虛聲,惑騙群眾。何況他出家不久,有什麼道德修持可言呢!」那位老居士臉色沉了下來,嚴肅地說:「你既然是一位修道之人,見人有德,應當讚揚,知人有過,應當善隱。這樣嫉妒同行的道友,如何能稱為修道之人。」
這時有一居士從外面進來,他認識我,高興地對我行禮。那位老居士見狀就問:「你認識這位道人?」答說:「這就是肖園還極師。」老居士說:「差一點當面錯過!」他立即告知主僧和各位會首,一齊向我作禮問好,並且懇請我主壇。我說:「主持龍華法壇者,應該通曉玄門法事,我只是靜修,專門禮誦,不宜。」他們一再誠懇請求不已,我也推謝再三。後來,我見眾人情堅難卻,就說:「此大法會,必須以齋供僧眾為首要任務。你們可曾作好準備?」眾人答:「沒有準備。」我說:「如果缺了齋供僧眾這一條,怎麼能稱為勝會呢!這件事,我將勉力承擔下來。一來與眾居士共同莊嚴道場,二來可引導所有善信之人佈施植福。」大家聽了欣喜拜謝。
第二天準備去拜訪該鎮的知名人士,勸請他們帶頭讚助此次法會。有人說,本鎮有一艾姓家族,為鄉宦,另有一呂家,官為指揮。兩家聯姻,為翁婿,都是富戶而且好為善事,又是浪穹縣肖暗初家的至親,此外就沒有人可比了。我一想,此事看來有希望,就決定先去拜望呂家,在門口恰好遇見肖暗初派來送禮的人,我就順便請他進去通報一聲。我被請了過去,艾護法也正好在此,他雖聽說過我,卻未曾見面。我敘說了法會齋僧之事。艾護法說:「哪裡有建龍華法會而不齋僧的道理。還極師既然肯一肩承當此事,老夫也願帶頭倡導。」他馬上就派人邀請本鎮有德望之人和善信之士前來共議,大家都樂於隨從。
第二天,艾、呂二位護法,擎著一青一黃兩把蓋傘在左右,我身著道袍草鞋在中間,後面鄉耆善信隨行,把該鎮大小街巷周遊一遭,各自勸請親友共成善事。當日所施之錢物,共計有銀錢三百餘兩,米五百餘石。
回寺後,即時聘請工匠,起造草房數十間;其它一應什物用具向各家借用,只有主管伙食一事,很難找到合適人選。到了下午,有一行腳僧來,相貌古樸,語言柔和而有力。問他從哪裡來,說是前去朝禮了雞足山而來,是尋甸府人,法名成拙。我請他相助,他當即允應,很有道念,他日夜操勞,全無一絲輕慢倦怠之意,彼此我倆成了志同道友。每天前來趕會吃齋的雲水僧道,不下千人,孤寡男婦乞丐貧人超過百數。凡是前來設齋供僧的施主,我都勸請他們禮敬僧眾求福。又向他們開示說,那些貧苦人中,不一定就沒有我們以前多生多世的父母及眷屬。因為他們前世不供養三寶,不濟救貧苦,所以今生招來這樣的報應。你我都是肉眼凡夫,看不到這一點,應當折服高傲我慢的習氣,恭敬禮拜。他們聽了都很信服,依言而行。這是滇南地區,自古以來罕有之事,也是我未習經典,出自己意所作的教化開導因緣。到了法會將要結束時,聽到各位會首私下議論,要準備禮物酬謝我。法會圓滿的前一日,我就私下向成拙一人辭別,乘天色未曉,一人悄然返回浪穹縣。
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我三十歲。二月中旬,劍川州當時有李君輔和李君弼弟兄,都是學界名士,篤信三寶,常和我會晤。他們有一書室,離劍川州城三十多里,青松蒼古,赤岩奇秀,極其幽僻,想請我去那裡靜修。他倆與肖暗初交誼甚厚,就派人送信給暗初。暗初開始猶豫不決,從道友感情論,難於與我離別,從儒友交情想,又該滿足李氏兄弟之求,因此兩難。我說這裡離劍川不遠,還是捨己從人為美。我就辭別肖園而應請去李園。三月十五日抵達,在那裡齋僧如前,修道益加精進。李氏兄弟增加了信心,其兄也發心畢生吃素了。
六月初,天氣炎熱,我為納涼,攀登至赤岩上,找了塊巨石,盤腿而坐。向西一望,只見約莫五里遠的地方,群山環抱之中,樹林蓊鬱,想必是一座古剎。就起身向那裡走去。到了那裡,只見一座茅廬,竹扉半掩,從裡面傳出木魚咜咜和喃喃誦經之聲。等到經聲停止,進去見一老僧,儀容可敬,我就禮拜。他說:「你們黃冠(道士)之流,多不禮僧。你從什麼地方來?名號是誰?」我說我是浪穹肖園的還極,現今受請住在赤岩書室。他就拱手問訊,說:「聽說還極師在三營龍華會中,齋僧濟貧,不分門戶貴賤,並且善於開導施主和信眾,空去我相。請問你拜誰為師?看什麼經教,能這樣作廣大佛事?」
我說:「未曾拜師,也未誦閱佛門經教,全憑自己的意思這樣做的。」他頗感驚訝,說:「你所做的,都是菩薩行,你大有慧根,快些拜位明理之高僧為師,剃髮為僧吧,以便弘揚佛法,化導眾生。我常誦讀《華嚴經》,你可以請去,恭敬跪閱。佛、道之理,有淺有深,而菩薩的悲願行持是無量無邊的。你自然發菩提心,不用藉助於別人的開示。」我聽後拜謝並請了《華嚴經》回到赤岩,焚香跪閱到「世主妙嚴品」完,就回想起最初出家時夜裡所作之夢。想披剃為僧的心情,驟然急切起來。
七月終,浪穹縣大寺主僧妙宗,帶了肖暗初的信來會我,邀我同朝雞足山,這正合我意,立即辭別李氏兄弟,會同暗初和妙宗二人,於八月十五日到山,夜宿寂光寺。打聽山中有無明師,聽說獅子峰有大力和白雲二位老和尚,精修淨業,三十年不曾下山。我便於十八日同妙宗和暗初,穿松林,繞溪徑,下山谷,登峭岩,到達了靜室,禮拜哀求為我剃髮。大力老和尚詳細問了我的根底和緣由,幸得垂慈應允,命我準備衣缽。暗初就說:「既然承蒙和尚攝受還極,他的衣缽齋供等事物全由弟子我承擔。」白雲老和尚說:「我觀此人終究要成佛門大器,不可草草行事。恐怕出家容易,持戒不堅。必須要他自己沿門乞討化緣,以折服他的我慢習氣,考驗他的心志。乞化得了衣缽,再回山披剃。」我心想這兩位善知識,一個慈悲攝受,一個要折服我之貢高慢心,實在令人敬畏,佛門全然不同玄門(道家),慎重而不氾濫,心知因緣未到,含著眼淚說:「和尚所說,一一遵依。但既然登山來到此地,我不忍空手而回,求和尚慈悲,賜我一個法名。我雖未剃髮,暫且作一名心僧。」大力老和尚聽了以後,破顏微笑,就給我起了法名書瓊。
我禮拜之後退了出來。心中想到下一步應當怎麼辦,正在躊躇之間,有一僧人名月峰,走上前來問我:「道人,你心中有什麼事委決不下?」我說:「正在想到哪裡去乞化衣缽,沒有熟悉的地方。」他說:「從浪穹縣出發,過鳳尾山二百里,有個地方叫落馬井,產鹽,有數萬戶人家,好善多富。我就是那裡的人。最近幾天我要回去拜省我的師父。我想你沒有去過那地方,可以一同去。」九月末,就與月峰離開雞足,向鳳尾進發,走了半個多月才到落馬井,住在西山放光寺。主持僧悟宗,歡喜地接待我們,不像初初會面的樣子。這寺是楊雄家族的香火廟,一家世世樂善好施,晚輩子侄多半從事儒生之業。又加上月峰和悟宗兩師的讚歎促成,所以善信們都來相助,又有當地土官名自晏之,和我一會,非常投機,彼此十分愛敬。
原本來到的是生地方,反而成了熟熱之地。我急切想回雞足山披剃,卻一再被當地善信施主們挽留。到了崇禎五年九月初(公元1632年),有一位省城的亮如老法師應邀去永昌縣講經,圓滿後返回省城,正好從這裡路過,住在東山大覺寺。我就和月峰商議說:「這裡的善信施主堅留不放,我出家之志未遂。我打算隨從亮老法師剃髮,以便隨侍在他身邊參學。但又擔心這樣做違背了想在雞足山披剃的本願,背信於大力老和尚。這事該怎麼辦呢?」月峰說:「我知道,亮法師是寂光寺那一法派的人,曾在寂光寺作方丈三年,你的法名,也屬寂光宗派,若在亮法師處披剃,看似離了雞足,但就法派而論,仍然是大力老和尚之法孫,不能算背信,還是滿了本願。應當速辦,不要再遲疑不決了。」於是我才下了決心,就和月峰離開放光寺,下西嶺、登上東山大覺寺,禮拜了亮如法師,只說前來瞻仰供奉,不敢放肆直說要求落髮。承蒙亮法師恩允,就移住到西山放光寺。
第二天一早我焚香向亮如法師哀懇為我披剃。亮如法師笑著說:「我昨晚夢見一僧,身著袈裟,隨從之眾無數,對我說頭髮長了求我給剃去。今天應了這一因緣。你是再來人,可以紹吾(繼承我)弘法利生,應該取名讀體,號紹如。先選定吉期,備好五衣,受根本五戒。」我深悲自己出家太晚,但可喜的是我宿有深因。就卜算決定十月初五日披剃。街上的善信男婦,在當天接踵登山來寺隨喜。我正在為缺少幫手著急,信步走出寺門,當面就撞上了成拙。我們三營鎮一別至今已有兩年,今天相見,恰如早有定約。問他從哪裡來,他說,「從永昌府寶台山來,想隨侍亮老法師。昨晚趕到山下,聽說法師在放光寺,今天要為一道人披剃,原來是你還極師喲!」兩人大笑,真是不可思議的奇緣。巳時(九點至十一點間)擺設好法座,舉行了披剃受戒儀式。很多男婦圍座觀禮,如觀至親,嘆息依依,不忍捨離,齋供完畢才散去,一路上只聽佛號聲綿綿不斷。
第二天晚上,月峰說:「這個地方的善信們持誦佛經的人多,但從未見聞法師宣講。紹師若肯承當講經,請亮老法師慈悲肯允,那麼就永遠不會忘懷在此處披剃的因緣了。哪有人正逢飢餓之時,遇到美膳而不想飽餐一頓的呢!」因此我就把月峰師的提議,向亮如老法師呈報了,並表示自己願意作期主。師允許我講《法華經》。就從初十日開始,講經期間,期場所用什物,都向土司自晏之借用,日用錢米,由百姓自願捐助。我白天作期主講經兼作知客接待工作,夜裡研讀經文,第二天上座宣講。司庫內勤工作委託成拙師,外辦採購全由月峰師作主。每天聽經的四眾甚多,三頓粥飯和素餚,無有短缺。到十二月初八,講經圓滿,錢米有餘,既有利於眾生,又增加了信心。
初九日,向眾施主和護法作了告別,初十日我便隨著師父出發,十五日抵達浪穹縣,住妙宗寺。肖暗初因出遠門未晤,楊紹先得知後把我們接到他的書院中安居過年。有位同行的道友名遍周,鶴慶府人,是龍華山棲雲庵的僧人,見到我初出家就作了講經期主,主動請求宣講大法,他亦發心恭請亮如師到棲雲庵講《楞嚴經》。師父慷慨法施答應了。正月十五日以後,我向楊紹先並諸舊交辭別,看到我必不可留,就贈送路費,我一概謝絕,大家感到掃興,因此只收了少許。亮如師見我淡薄財利,息滅貪心,對我就更加慈愛。
二十二日到棲雲庵。麗江府上官姓木,篤信三寶,當地的規矩規定不准出境,但聽到有善知識和法師來到鶴慶府,他就派人迎請入境,所以就前來恭請師父。我就隨侍師父同去。麗江府的地界東止金沙江,西至黑水河,南接劍川州,北臨土蕃(西藏)。土官的府院倚建在雪山下,銀峰高聳虛空,翠林鋪滿大地。留住那裡半月,隨時請問佛法。
二月十八日,我們辭別返回鶴慶府,二十日開始講《楞嚴經》,我有幸被指派任職後堂(內部)工作。劍川州瞭然法師為首座,他是石室山萬佛寺僧,幼時曾去江南各講堂參學。這一期講期,由四位堂口班首輪流復講。當瞭然法師復講到八還章時,超越了原經旨意,推翻貶低正座亮如師,眾人不服。西堂班首一雲的話激發了我一時衝動,就在講堂當眾揭露首座瞭然的過錯,用清規石處罰他。亮如師父知道後下得堂來,詢問原委。眾人說:「首座欺昧良心,後堂性情耿直。兩人都未向師白告,乞求師父慈悲饒恕。」亮師對首座說:「八還章,文字道理顯然明瞭,是你譭謗經法,自招眾忿,自己應該明察這一點。」又對我說:「你不奉師命,擅自動用清規,應當重加責罰。現在根據眾人的評論,從輕處罰,跪香一炷。」又對眾人說:「後堂紹如認真維護經法,就來領眾出頭。只知道規矩可行,就不知道人情可諱。」
有一天,來了二三個初出家的到庵上聽經,一派世俗之態,令人厭惡。亮如師勸誡他們說:「出家必須先受沙彌戒。再受比丘戒,行住坐臥應當具備諸種威儀,才能稱作僧。若不受比丘戒,威儀不具,不能叫僧,玷污了法門的清譽。」當時我正侍守在亮如師旁,聽了以後就向師父禮拜並說:「請師父為我授比丘戒,使我得成合格之僧。」師說:「我是法師。受比丘戒,必須請律師。」我又問:「誰是律師?」師說:「律宗現在快失傳了。南京有古心律師中興律宗,被尊為律祖,他已涅槃。他的傳法弟子中,只有三昧和尚在大力弘揚毗尼(戒律),現在江南。」我說:「我去江南受完戒,再回來侍隨師父。」師說:「萬里迢迢,你說得輕巧!」我說:「師父您說的,不受比丘戒不能叫僧。我捨離道門,歸依釋教,為的是作一名僧人。若不能成僧,剃髮還有何意義!」師父沉默無言,我也就退了出來。
我就這樣經常向師父求告,師父每次都不發一言。到了四月八日講經期圓滿,我在午後又去方丈室向師父告假。師父見我念切志堅,就說:「這是你業力所牽。前途是福也要去受,是苦也要去受。你就去罷!」當時另有幾個人也想和我一起去,也都向師父告假。師父說:「你今天剛開始行腳,就有多人相隨。以後學得好,你會成善知識,否則就成江湖中之頭頭。」我拜謝說:「承蒙師父慈悲授記。我從此要去學作善知識。」
崇禎六年,我三十二歲,四月初八日申時,離別棲雲庵,走了二十五里,到一小庵借宿。成拙二月中旬先上雞足山,我們相約四月二十日在大理府三塔寺相會。我按時到達三塔寺,未見成拙。第二天我去感通寺隨喜,成拙才至。從此,我倆南下相伴不離。走了四天,到了北岩山谷鳥寺,遇見一位在俗時相識的熟人,已在該寺出家,正在施茶。他見到我很驚訝,說:「你怎麼出家行腳啦!我自恨年紀已老,不能隨你同去!」我勸他專修淨業,他立願念佛終生。在此住了十天,便告辭啟程而去。
到五月初二日,遙望白雲,家鄉已在目前,借宿在離城十里的金贍寺。思想起自己雙親不能奉養,伯父不能親葬,通宵雨淚不幹。又想起拋撇下兩個幼小的弟弟七年之久,不知流落到何等悲苦地步,現在依附在誰家!我這一別遠行,不知今後如何。不能不見一面。天明我向成拙述說了我的心事,出門走了幾步又停了下來,一再思前想後,悲嘆不已!想到,如果現在還以手足之情牽掛,一見面必然墮入業力之羅網,不但出家受戒修行不成,而且今後要報父母、伯父生育深恩也就無門了,應當看到各人都有各自的定業因緣。凡是人生在世,貧富苦樂、壽命長短,都是前生自作之業所感,今世各自受報,縱然是父子至親,也不能替代。只恨不能前去親見一面,這是忘仁義而缺慈悲。現今無可奈何之下,只有用自己修行功德,迴向給他們,拯濟他們了!於是我擦乾眼淚,繞城而過,遙向西山祖宗墳塋,倒地叩首,心痛如絞,雨淚不止,兩足無力,難以舉步,勉力奔走,到了廣通縣,在一座古寺中掛單一宿。
第二天,在去祿豐縣的路上,遇到一位親戚周之賓,從省城返回楚雄。他老遠見到我就高聲叫道:「許沖宵,你現在什麼地方?幾時出家?要到哪裡去啊?」我答說:「在雞足山出家,現在下江南去受戒參學。」他問:「是否有信要捎回去?」我說:「捎信也說不清楚,只有二個幼弟,還請你多加照應了!」我一面回答,腳下並未停步。他還想再問些什麼,我心中悲慼,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他站在路邊,望著我走遠才反身走去。成拙說:「既然你不回去相見,也該捎個口信回去才對。」我說:「手足親情,要斷立斷,要捎話去,反而惹起情思難斷了。古人云,心如鐵石,志願方堅;情愛不忘,至道難成。」
又走了幾天,省城在望,進了碧雞關。此關峰巒秀拔,為群山之首,俯瞰滇池,一碧萬頃。我們搭船渡過滇池,登岸到了省城,投宿在城外彌勒寺。同行的幾位朋友想到各寺廟去瀏覽,打算在這裡歇息幾天。我擔心會碰到親友而遇阻攔,第二天一早,就動身去松華壩,出金馬關,到達板橋驛,住了一夜。成拙的俗家住在尋甸府,在楊林以納寨的觀音庵出家,因為是便道,離此不遠,就邀請各位朋友一起去看望他的師父,然後再遠行。我們過了兔兒關,在何有庵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到。他的師父厚道,他的哥哥朴實,都是修道之人。他們一見,歡喜相迎,款待挽留我們住了半個月,方才告別。
走了幾天,抵達曲靖府,來到破秦山,是當年諸葛武侯與孟獲盟誓的地方,有一古寺,我們就在這裡掛單。我對各位同行說:「我們大家這次遠行,並不是泛常的遊方僧,不能只是到處觀賞風景,不務正修,應該在這裡購置一架羅漢燈,上面是燈,下部貯油,白天挑著,夜裡照明。每晚大家輪班守值,吃完晚飯戌時點燈,大家圍坐燈前,各人按照自己所學之經,或者讀經文,或者體味經旨,到中夜放參,作為我們行腳的定規。」大家一致同意遵行。
來到平彞衛,出滇南勝境,就與貴州接壤了。走一自孔(亦資孔),進了普安州。又走了幾天,過關索嶺。此嶺地勢極其高峻,周廣有百餘里,嶺巔建有一座軍營,還有關索廟。又走了幾日,過了盤江,山路屈曲,上下陡峻險惡。頃刻之間,大雨滂淪,山澗小溪變成吼聲如雷的山瀑,彎曲的山路都成了河溝,狂風從多方吹來,形成漩渦,單身難以直立。雨水從頭頸瓢潑而下,灌滿衣褲,寒徹肌骨,兩腳橫跨而行,如騎浮囊。解開衣帶瀉水,猶如開閘。像這樣有好幾次。我對各位說:「古人參學,捨身求法,不以為苦。不要因為這場大雨而退了求道之心,將來才好對人家誇耀我們行腳何等英雄!」大家聽了大笑,你扶我攙,相助而行。天將傍晚,才到山下,住宿大願寺,遇見一位從江南來的僧人,就向他了解路途之上的情況。他說:「現在行腳最難,到處都有江湖團夥,多作魔業,見了穿衲衣坐蒲團的僧人,則不加侵害,否則恐怕參學就有障難。我勸告各位朋友,若想圖得一路平安清靜,只好把你們的行李更換一下。」我們歇息了十天,過了盤江渡上之鐵索橋,只見山崖險峻,樹林竹叢鬱鬱蔥蔥,滔滔江流奔激如箭。這正是連通雲貴的要津。
第二天,上了通向安莊衛的山徑,砂石凸凹,峻嶒盤曲,不覺鞋底磨透,踢踏著難以再穿,乾脆扔掉,光腳走路。走了數十里,天晚才歇息,雙腳腫得沒有了腳踝,疼痛得猶如火燒錐刺。半夜裡想道,身無分文,此處又是孤庵野徑,無處可以化緣,不應在此久留,明早必須動身。又想到世人為了貪求功名富貴,尚且得要忍耐不少辛苦,才能遂願。我們今天為了出家修行,求解脫之道,難道還能因為少了鞋穿就退了最初發下的願心嗎!次日仍舊咬牙強行,開初腳跟痛得不能點地,拄著棍杖踱著走,漸漸走了五六里,就感覺不到還有雙腳,也不覺痛了。途中又沒有歇息之處,到了傍晚,已走了五十餘里,投宿安莊衛庵中。第二天乞化到了草鞋,試著穿,皮破繭起,我也不管它。有一江湖中人跟隨我們走了幾天,歇息過夜都不離開。次日午後來到一小河,上有獨木橋,長兩丈多,成拙等人先過,我慢慢走在後面,那人也尾隨而來。正走到橋中間,我突然口頭大喝一聲,他嚇得掉落水中,我指著他說:「你該從今以後洗心革面,作個好人。」他面紅耳赤,爬上岸,垂著頭抄另一條路走了。
路途之中所遇種種艱辛,同行諸友都不覺為患。夏去秋來,於十月初,才到了湖廣武岡州,投宿在止水庵。主持僧名異卉,極有道念,了解到我們從雲南遠道而來,就留我們住下過冬。一天,他請我入房喫茶,我見案上有一部《法華知音》,在雲南時我曾聽師父稱讚過這部書,所以腦子裡有印象,就想借來抄寫,可是沒有紙筆。主持的師弟法號中立,很好學,看懂了我的意思,就提供了一切所需。這年的冬天,每日大雪不止,加之屋內空曠,北風嗖嗖灌進房來,我只穿了一件衲衣,坐在掛單僧的板床上縮著頭抄寫,雖然手指凍得僵直皺裂,筆墨結冰,也沒有少許停歇。他們師兄弟二人,見我堅志勤學,愈發愛憐敬重,送了一件棉襖,我慚愧地收下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棉衣。同行之中有二三人告別了我們去朝海。成拙和覺心隨伴著我。
這個武岡州屬於封藩岷王的領地。有一個岷王的宗室,名煙離。喜歡鑽研書法和繪畫,與異卉師有交往。十月中間,他踏雪來到庵中,帶著一張大紙,貼在牆上,想畫一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圖,用木炭條起稿幾次,仍然拿不定主意。我站在一旁觀看,就說:「凡作畫,必須意在筆先,下筆不再思索猶豫,才能傳其神韻,像這樣再三揣摸不定,恐怕就失去了天然之妙趣。」他回頭看著我說:「說起來容易,作起來實在難。你能作到嗎?」我笑著說:「懂得一點。」他就把筆遞給我說:「請畫!」我接筆在手,先在心中打好腹稿,接著一揮而成,把筆放在案上。他深加讚美,對異卉師說:「出家人中,所隱高手不少啊!就把這幅畫掛在庵裡吧!」從此他常過來和我坐談。親筆寫了三卷字跡,贈送給我、成拙和覺心,敘說他到處拜訪高手的前後經過。
正月初五日,和宜法師在離止水庵六十里的梁家庵開講《楞嚴經》。中立師來邀約我們前去。成拙未曾讀過《楞嚴經》,就先往寶慶府五台庵拜訪顓(注3)愚大師,待講經完畢,他再來梁家庵和我們相會。我和中立師覺心等三人來到梁家庵,聽眾只有二十多人,每人各出米一石、銀一兩結社(打平夥)。中立師繳了錢物,而我和覺心只有隨身衲衣和蒲團,沒有錢米可繳,原本祇想隨喜一下就走。中立師就向法師白告,法師知道了我們來自貧窮的滇南,就免了我們的錢米,慈允我們隨眾聽講。我對覺心說:「佛法是法師所施,飲食卻是眾人出資所備,我們不能空受。」由此我們兩人自願於雜務,收洗碗筷,掃地擔水,不用人叫,有空就做。四月初一日,講期圓滿。中立就留住下來,我和覺心告辭後,前往寶慶府,投大報恩寺掛單。
聽說該寺內有一位自如法師,是雲南人,就去參禮,向他敘說了出家和南來的前後經過。自如法師就稱我為師弟。我問他為什麼這樣稱呼我,他說:「我是劍川州人,石室山出家為僧,少時曾跟亮如老法師學習經教,依止他老人家六年,深深領會到他的佛法教誨。到現在一直沒有互通音訊。今天見到紹如師,猶如見到了師父他老人家。所以若論法系,應呼你為師弟。你在雲南聽師父講什麼經?」我答:「曾聽《法華》和《楞嚴》,只是種了點因,並沒有領悟其義。」他又問:「今天你從什麼地方來?」答:「從武岡州梁家庵,聽了和宜法師講《楞嚴》後才來此處。」自如師說:「和宜法師是我的同參道友。這次你來得正巧,顓愚大師新出了一部《楞嚴四依解》,各位護法居士請求印行流通。大師命我在此寺代座宣講,聽眾已有一百多人。正缺少一個管理後堂的執事,師弟你可以擔任。」我說:「給我掛一個散單就足夠了,班首之職萬不敢當。」自如師說:「獅子之兒用不著過謙。我給你置辦僧服鞋襪,進堂主事。」我說,「求你應允兩件事:一,就讓我仍然衲衣蒲團入堂坐臥;二、懇請方丈不要經常令人給我加餐。只要能聽經教餐法味,我就感佩之至,無以復加了。」自師卻不以為然,非要我更換新衣不可。當時寺中有一常住僧,名野溪,也在聽眾之列,長期依隨顓愚大師。
第二天他前往五台庵禮見大師,大師問及講期中的事情,他就把我的來歷和所懇求之事,向大師呈白了。大師說:「我幼時在北五台竹林寺,依隨月川大師,隨眾聽講,也是衲衣草鞋,杖笠蒲團。後來開始行腳,天台、南嶽等地以及直到這裡寶慶,也是依然如故,不曾更改。因為檀越居士們建了此庵,他們跪地雙手捧著衣履求我更換。若不接受就長跪不起,所以我就聽從了,也是為讓他們生信。我經常看到禪和子(參禪僧人)不願改變這種習氣,都愛好這樣,難得看到願意別行一路的。今天聽到雲南來的這個僧人不被境轉(不為外部條件而改變自己的定心),真是有些像我當年的作法。你回去告訴自如法師,隨順他的本志,不要強迫他吧!這樣做可以教誡大家不應多貪。」自如師也就允許遂我所願。大眾之中,有讚歎我古樸的,也有譏諷我標新立異的。我對這些譏諷和讚譽,權作無聞。
講期開始後三日,方丈命四位班首復講,按輪流次序,每人要講六次。西堂班首因事外出,首座抱病請假。只有堂主(主持講堂事務)可度師,是南嶽荊紫峰無學大師的傳法弟子,生性醇厚好學,和我心志相投,彼此互相敬重。從《楞嚴四依解》第四卷以下,全由我們兩人輪流宣講至終。道場圓滿,自如法師帶領眾人去五台庵,禮謝顓愚大師。正好大師跏趺坐在傘下,所以他的別號傘居道人,自如法師禮謝大師之後,便回大報恩寺。大師把我留下,在傘下賜我一餐,菜是一盤苦瓜。大師先挾了一筷,同時叫我也吃。我送一挾進口,味苦難嚥,又不敢吐出來。大師見狀就笑了,對我說:「先苦後甜,修行作善知識也是如此。」我禮謝了他的開示。大師說:「你有點骨氣。以後打算去哪裡?」我說:「在雲南動身時,本為找尋三昧和尚求戒,受戒後隨便參學。」大師說:「三昧和尚是真正的律師,你可以去受戒。要說起隨便參學麼,江南叢林,多半講席都規矩不嚴,人多狂妄傲慢。如果感到不相宜,你還是回到我這裡來,千萬不要在外順流隨習放縱自己。你將來必為法門樑棟。」他當時就叫侍者拿來一套他自己譔寫的著作,送給我,並再一次告誡勉勵我說:「要學我的操行修持。」我拜受而別。
次日,我約成拙一同去朝南嶽。自寶慶府出發,走了五天,過楊柳塘,登後山而上,游九龍坪和古大坪,坪側有雉潭一泓。三昧和尚行至此潭時,有條龍化為雉雞,從潭心鼓翼而出,三昧和尚就為它授了三皈五戒。我們又參拜了茅坪等佛寺,繞過天柱峰、煙霞峰,從祝融峰下至南嶽廟前,在施茶庵掛單。在那裡,遇到一位行腳的雲水僧,我們就向他打聽途中情況。他說:「現在土匪猖獗,正在常德、潭州、公安、荊州等外流竄,各處防衛甚嚴。官兵也不好,常把僧人的行李搶了,還反誣之為奸細抓起來,有冤無處申,備受苦惱。各位師父千萬下不得山啊!」我和成拙聽後,心裡並沒有被嚇倒,心想難道徒步走了數千里路,白費力不成!就向庵主打聽,是否還有別的道路可通。他說:「世道如此之亂,還是先暫時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等太平了再走,不必心急!」我說:「我決心已下,時間不等人啊!請你另指條路,我就很感激了!」他說:「另外的路倒是有一條,只是非常荒僻,少有人走,一路上盡是山嶺深壑。必須從黔陽走會通。往呂林縣,過普安慈化寺,到了那裡再問去萬載縣的路,再到瑞州府,就可以到江西省城了,這條路可以避開流賊作亂之地。」次日早晨,我們照庵主說的路線啟程了。一路上果然山嶺重重,不見村舍,荒涼至極。有時清晨一餐一直走到晚,有時全無早餐就動身。每天行路不下七八十里。半個多月,才繞道來到江西省城,掛單在塔下寺,休息了三天,然後走德安縣,遊歷了廬山,參拜了歸宗、開先、五乳等寺。
一日,來到了萬松庵,天色垂暮,我們敲門借單,庵中之僧見了我們怒氣沖沖,把門砰然關上,不准。這時天已黑盡,明星朗照。無奈祇得找個處所過夜,見有一大石懸翅在路邊,石下有一丈多空間。我們三人擠進去,放下蒲團,坐著等待天亮。隔了一會,寺門又開了,那個僧人又來驅趕我們。我們三人自嘆無緣,反而憐憫那人太癡,但並未理睬他,強坐了一夜,東方將曉,三人起身順路而行,到了豆葉坪,吃了早食,接著遊歷了曬穀石、仰天坪,甚至還游了金竹坪,太陽將要西下時,到了東林寺掛單。寺內的禪堂在後面。雲水堂只有三間,冷落不堪,荒草遍地有尺多高,牆塌瓦脫,門窗都無遮擋。寺中有一無梁殿。我們進去禮佛,只見塵灰厚積,鴿雀之糞穢污。我與成拙把佛殿打掃乾淨,蒲團放在佛像左側,商量著準備在此念佛通宵,才不虛到此古白蓮社一遭。誰知當家僧從裡面走出來,指責我們不先白告執事,就私自住到大殿裡,大聲呵斥著趕我們出去,一直趕到山門。一位住在那裡的化主老僧留我們吃飯,讓我們住宿。那位當家僧又來責備老僧,還把地用水潑濕,不讓我們坐臥。我們三人就謝別了老僧,走出山門。
我對成拙和覺心說,多生多世以來,一定和那位當家僧種了不如意業因,今天該受還報,把他作善知識想,幫助我們成就忍辱行,千萬不能起怨恨心等等。但這時又找不到棲身之處。成拙說:「剛才來的時候,曾見下面路上有一稠密樹林,可以去那裡住一夜。」我們就下去尋找那片樹林,卻是一個古墓。三人放下蒲團,席地而坐。曠野空蕩蕩寂靜無聲,又無月色,黑洞洞不見五指。坐到初夜時分,忽聽一聲:「抓住他啊!」四下裡一齊喊叫:「抓賊啊!」我對成拙覺心說:「如果他下毒手追來捉我們,皂白不分,有口難辯,就是我們的定業了。」
待到天明,遠處傳來差馬的鈴聲,才知道外面是大路,心裡才稍稍安定。三人走出樹林,見田中有人在勞作,上前問他,為什麼昨夜四處齊聲喊叫,他說:「現在田中麥子熟了,防人來偷,所以齊聲喊叫,為的是嚇唬盜賊。」我們三人大笑起來。
我們隨即到西林寺參拜,過了一宿。次日到了九江府,太陽已沉西,城外各庵都拒不留歇,說是地方上嚴禁外人留宿,讓我們過江去,那裡可以住。我們只得忍饑渡江。船到江心,渡船工要錢,我把捆腳帶解下來給他。同渡人中有一道人見此情景,替我們付了船錢。登岸以後,向旁邊的人打聽,附近有無投宿的地方,答說近處沒有庵堂,順著江堤下去七十里,到鑿港,那裡有一地名叫五祖離母墩,有一座茶庵,接待僧人。我對成拙、覺心說:「咱們被人騙了。前面的茶庵又遠,西南風又刮得緊,只好勉力快走,不要在這裡猶豫停留了。」三人頂著烈風,掩著口面,在月下急走,後半夜才趕到。敲門求宿,幸虧主持僧道心慈悲,馬上起來開門,請我們進去,問我們為什麼深夜行路,我們把詳情說了一遍。他長嘆一聲,感慨行腳之苦,高興地為我們烹茶。我讚歎道,若不去九江的庵堂,怎能顯出這裡的道心呢!
第二天早食之後,向他了解前去一路如何走,才知道一路上各個祖庭殿宇都頹敗了,幸虧三昧老和尚把它們修葺(注4)重新。我們決定前去隨喜參拜。就出發去黃梅縣,登破額山,參禮四祖道場,又再到馮茂山,參禮五祖道場;上高山寺,禮淨鑒祖師道場;過鈴鐺嶺至老寺,禮千歲寶掌祖師道場;往潛山縣,禮三祖道場;到青陽縣,朝九華山。從大殿下望,有一庵,就前去掛單投宿,但不供晚餐。第二天早上,我們坐在那裡很久等候早餐,只見主持僧來告訴說:「庵中淡薄沒有財力,只安空單,不供齋飯。可去房頭那裡化齋飯吃。」我對二位道友說:「房頭是葷廚,哪裡會有淨食,到別處去吧!」隨即上殿禮拜了菩薩,空著肚子下山。走了十多里,到一宿庵,才吃了點東西。
我們來到太平府,聽說融悟法師在青山寺講《法華經》,離府城不遠。我們欣然問路前去,到寺時太陽已經落山。當家僧見我們都是杖笠蒲團,不給安單。求之再四,他見天晚難行,就叫人把我們帶出山門外,在路旁一個小土地廟裡住宿。三人把蒲團相重,對面而坐。我說:「既然我們為求法而來,怎麼能空手而回呢!」次日一早,我們仍然走回寺去,吃了早粥,聽經一座,就下山去,向村民乞食問路,又繼續前行。於初十日巳時許,到了南京。遙見報恩寺寶塔,五色凌空,映日生輝。進內頂禮繞塔,到了中午,腹饑無食,就問禮塔的人什麼地方有接待僧人的齋堂。有人指著南廊三藏殿說:「那裡就是。」我們去到那裡,禮佛畢,坐在殿台階旁,只見有僧人進出,卻無人上前招呼我們。我們三人不知這是什麼原因,就起身出門,遇到一老僧,向他打聽其原因,他說:「南京是講席禪堂,如果衣履整齊,是禪和清客,就有人接待。你們是遊方僧行腳的,所以無人過問。」
我們遂即進城,到鐘鼓樓西大佛庵掛單,那裡沒有大殿,只有一蘆蓆篷遮在佛像上。庵主是實修之人,以一盞飯接待僧眾,很高興見到我們。知道我們從雲南來,就說:「這裡興善寺的當家,法號印吾,是你們的同鄉,可以去那裡,自然會留你們住宿的。」次日午,我們到了那裡安單。見大眾吃的都是蟲蛀陳倉之米,菜只是少鹽的臭薤之類。我們進到客寮隨喜觀看,見到他們本寺常住眾人,吃的卻是時鮮蔬菜和白淨米飯。當家之徒名廓然,也是雲南人,聽到我們的口音。晚上他來雲水堂認鄉親,我說我們是貴州人。他又再問,像是要留我們住下。我對成拙和覺心說:「咱們迢迢萬里而來,應當依止有道德的善知識,像這種不為眾人著想的人,我們寧可甘願清苦,不可以親近。」
聽說覺悟法師在園覺(注5)庵講《楞嚴經》,就出城去聽。正遇上有善信施齋供僧。凡是十方來庵之僧,都在韋馱殿就地板而坐,每兩人四木碟菜。我和一位遊方僧共一處用齋,我自己注意威儀,緩慢進食,他卻筷子不停,一口氣把四碟菜全部吃光。齋畢出門,我對二友說:「咱們以後,若有因緣為眾設齋、菜不論有幾種,都盛做大碗,讓大家隨便吃。一則使大家都注意僧人威儀,二則也可使眾人信敬。像今天的這個人,真是僧格喪盡,與餓夫有何區別!」
我們又去普德寺參禮隨喜,進禪堂掛單。晚上我們商議說,現在十月將盡,路上行腳太冷,不如在此暫住,春暖再走。次早吃完粥,向寺內都管討單,他說:「兩個人一起都不能給單,何況你們是三個人。」他又看著我說:「鐘板堂的香燈單,給你一個人。」我笑著說:「我這人粗手笨腳,不會剔琉璃燈。」三人就收拾行李出了山門,我對成拙、覺心說:「京城的叢林既然三個人都不給單,我們暫且各自分散過冬,約定在臘月三十日相會。聽說寶華山重視學習經教,我想去學誦楞嚴咒。」成拙說:「我和覺心去祖堂,你學完咒就過來。」我把蒲團與覺心換了一條臥褥,三人就分手了。
我上到寶華山半坡時,太陽已落山,投宿石門庵。晚間喝茶時,我問主庵僧:「聽說華山很重視經教的學習,我想去。」主人說:「山中有一老首座師,是雲南人,常在北都。來到這寶華山已十年,閱大藏經已三遍,最喜歡勤奮學習的人。我也曾隨他學經。寺里人很少,有四位房頭,幸好大家一鍋吃飯,不另作菜飯。雖然三餐都是薄粥,來往朝禮銅殿的雲水僧人,都接待食宿。你既然想住山研學,應須把身心放下,不要嫌那裡清苦淡薄。」次早上山,到了常住(即有常住僧人主管的寺廟),禮佛畢,便去各處隨喜並禮見常住僧人一天。隱隱之中,感到這裡很熟悉,似曾來過。拜見了首座師,頂禮畢,說明想學楞嚴咒。師問:「你是什麼地方人?出家幾年了?這個咒應該預先熟讀。」我說是雲南人,剛出家就到江南來了,又不識字,所以沒有讀。師就答應了,說:「你既來山中,可以去行堂(洗碗送飯等雜活),在廚房安單(住下)。」
到了十一月,天寒地凍,清洗了的碗疊在一起都凍成一塊,難以分開,我就每次洗完後,用乾淨布擦乾,第二天早上用時,容易分開。水單(挑水)一人供應不暇,我也幫著挑水。廚下典座(管理廚房事務之僧)法號瞭然,年輕伶利。另有房頭(掌管庫房之僧)每天把米和菜蔬量出,交廚下典座做飯,或煮菜。這些東西一經典座之手,他都要扣留一些。有一天,我背誦《楞嚴咒》回來,他留了飯請我吃。我問他:「大眾吃的是粥,這飯是從哪裡來的?」他說:「好心好意留給你,你反而要追問!」我說:「大丈夫豈能吃來歷不明之食!」起身就走了出來。從此以後,廚下之人都抱成一團,互相包庇,難以容我共住。那位典座私下裡與都管(總管)商議,板堂(寺中執掌報時的殿堂)無人,就讓我去值守,看香接板(古時以燃香計時,到規定的時候鳴板發信號)。這間殿堂空曠,僧床廣大,我一人獨睡,就像在冰窟裡一樣。有一房頭老僧,是閹宦出家,最有慈悲道心,憐愍我志高守貧,一日黑夜推門進來,貼著我耳朵悄聲說:「此件東西送你御寒吧!」說完就走出去了。
我伸手一摸,像似棉絮但不柔軟,蓋在身上一點也不暖和。天明一看,原來是一床補了無數補了的舊棉絮。東西雖說不好,但我十分感念他的慈悲之心。到十二月十六日,學咒完畢,我前去禮謝首座師,師父說:「開春元旦(大年初一),河口鎮一位桑居士,要來寺裡禮拜梁皇懺,你應當把咒讀熟。懺資可以治辦自己的衣履等用物。」我曾和成拙、覺心約定這天會面,也就無心於此。到十二月廿(注6)八日,拂曉時分,我起身向首座師住的寮房拜了三拜,回頭就下了山。到了東陽,打聽去祖堂的路。走了一百多里,太陽落西,群星映空之時才到,問成拙、覺心在不在,執掌雲水堂的主僧說:「幾天以前,他二人相隨去朝南海了。走時曾留下口信,若華山紹如來找,就讓他隨後趕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動身,過牛首時,逢見化主頓修,我們曾在貴州水月庵相識,他堅持留我過年。次日吃了點東西,我就不辭而別,到達靈谷寺,正是臘月三十日晚,雲水堂中多半是江湖幫中人,喧囂擾雜之極,又無空處。我就在門扇背後坐到天明,吃了早粥,就出發了。
出門遇見該寺當家,法號弘傳,對我說:「今天元旦,為什麼就走了呢!請回寺安息幾天吧!」我見他道誼殷切,就又回到寺裡,用了午齋,還是離開了靈谷寺。走了二十里,投宿在一個小庵裡。初二日,歇土橋南庵。初三日,在路上忽然遇到成拙。我問他:「你們二人同去朝海,怎麼你一個人回來呢?」成拙說:「覺心到了無錫縣先去海上了。我後到杭州,聽說三昧老和尚在五台山舊路嶺傳皇戒,所以返回來找你,一起同去。」我說:「五台山路途遙遠,是否真傳皇戒,還不一定落實。還不如就在南京古林庵受戒。這古林庵是律宗祖師古和尚(古心和尚)開創的道場。你看怎麼樣?」因此我兩人來到古林庵,說來受戒。知賓師(寺中專管接待外來人員之僧職)說:「要想受戒,每人交單銀一兩五錢,衣缽自備。」
成拙有衣無銀,我是銀衣都沒有,懷裡只有一串滇南產大密蠟金念珠。就拿出來,交給知賓師作掛單製衣之用費。知賓師接到手,好像答應了,轉身走進房去。我的眼睛和耳朵都還很靈敏,見窗裡有人向外偷看我們,聽得裡面說:「這兩人是江湖,恐怕念珠來路不明,千萬不能允許他們掛單。」知賓師走出房來說:「常住辦理這些事情不方便,還是啟備好了衣缽再來吧!」我接過念珠轉身就走,他留我們吃飯,我說:「是龍終須歸大海,還能困在牛蹄窩子裡!」馬上走出寺來,另找了一個庵子投宿。次日渡過長江到了浦口。
正月十四日宿紅心鋪。傳聞流賊過來了,男人婦人涕哭,一片嚎哭之聲,拋兒棄女,慘不可言。我和成拙滴水未進,腹內空空,從早到暮,疾走了百餘里,宿三鋪。十五日夜,流賊攻破鳳陽城,燒燬皇陵。成拙和我向北走,到了徐州,才歇下腳來。次日渡黃河,但無船,就坐在岸邊等待,直到中午,見有官差馬隊,捉得船工和船過來,我們就順便搭渡。行到中流,大水湍急,船工喝醉了酒,手軟無力,船又破舊漏水。差官亂了手腳,連呼蒼天保佑,我們二人只專心念佛。幸好吹來一陣微風,把船飄入蘆葦叢中擱淺,我倆人手抓蘆葦,涉水登岸,在一荒庵中過夜。
第二天,開始長途跋涉,有時沖風冒雨,有時戴月披星,或者去村莊中乞食,或者向耕夫化餐,於三月初一日方到長城口,一過了龍泉關,踏上了山西地界,最後到了五台山舊路嶺。這座寺接待來往僧人的十方堂,設在山門外。我和成拙兩人安好單,就前往方丈室參禮三昧老和尚。有兩位北方的僧人守門,對我們說:「有香儀(敬香的錢),可以進去,如果沒有,就退下。」我們看他語氣粗硬,難以理喻,就返回十方堂,嘆息不已,說:「我們登山涉水不遠數千里,前來親見善知識,現在因為沒存香儀而不能參見,這如何是好?!」成拙說:「不必憂心煩惱。明早等守門人去吃粥時,我們自己進去禮拜。」
次早,我們不吃早粥,忍著飢餓,直入方丈室頂禮。和尚問:「你們兩人從哪裡來?」答:「從雲南來。」又問:「來此作什麼?」我們因為沒有衣缽,不敢說來求戒,只說來是為了朝禮五台。和尚說:「文殊菩薩就在你們那裡,反而來朝台!自己實念修行去吧!」因此我倆發願,今後如果做了善知識,絕不收受外來僧人之禮儀,也好讓那些清貧的禪和子們容易相見。
我們就上了山,到了塔院寺。這寺裡有兩個房頭僧人是師兄弟,發心誦五大部經三年。問了我們,知道是雲南遠道而來,很歡喜讓我們留住。成拙自願擔水供僧,讓我進堂內誦經。他擔完水,專讀《法華經》。我除了上殿作佛事之外,空餘時間就閱《楞嚴義海》。我們二人口不說閑話,腿不胡亂跑,每天到中夜才放參(休息)。五台山上各大小寺廟,都以燕麥粉調成糊粥為食。塔院寺方丈師,法號德雲,以及房頭眾僧,見我們兩人如此勤學,一個多月下來無絲毫改變,都對我們產生了信敬之心,私下裡請我們吃米粥。我和成拙商量說:「我兩人在眾僧人中深夜研學,會打擾他們的睡眠。那邊伽藍殿(供奉寺廟護法神的殿堂)裡,晚上點著琉璃燈,裡面沒有人,我們不如到那裡去就琉璃燈光研習,這樣既不妨礙別人,我們也心思寂靜集中,利於記憶,學到夜靜時就停止。」五台山上春秋兩季尚且很冷,何況是冬季了!到了十月間,我們的衣著又單薄,手捧經卷,直立在燈光下,集中心力用功時,什麼都感覺不到。到得掩卷歇息時,手指僵直不能屈伸,雙腿凍木難以邁步,通身抖顫,寒徹肺腑。雖然如此,我們的志願卻更加堅強了。
開春正是崇禎九年。二月底,覺心朝海回南京,一路尋找我們,來到五台山相會。三月中有一個朝禮五台的僧人,是楚地(湖北一帶)人,法號皎如,我們曾在寶慶府,同聽顓愚大師講《楞嚴四依》,見我們在堂裡,就進來相見。有人問起他和我們相識的緣由,他把我行腳的詳細情況說了。方丈德雲師知道了,就設齋召集全寺僧眾,請我四月初一日開講《楞嚴經》。我承蒙厚愛,苦於不能推卸,祇得承當。到七月初一日方得圓滿。我們三人初來五台,就一直住在塔院寺,未曾朝禮五頂各佛剎,所以七月初三日先上東台。那裡的主持僧,用接待法師的禮儀款待我們。接著到了北台,當家僧還是這樣接待。因此我心中感到慚愧,其它幾台就沒有去朝禮了。
初八日,告辭了塔院寺方丈及各房僧眾,打算去北京向三昧和尚求戒。方丈師殷切挽留不捨,見到我們無心在此留住,就準備了三頭騾子,為我、成拙和覺心送行,並伴隨我們一直走到舊路嶺,留宿了一夜。次早德雲師仍然不忍分手,就又伴送我們到了棠梨樹下院。天明請我們用了齋飯,才一一拜辭。德雲師在分手時,眼含淚水一再囑告說:「受戒完畢,請還來五台,千萬不要辜負我們的切望。」
七月十九日到保定府方順橋西,投宿於羅睺寺。成拙在五台山時,曾與一滄州道人相約,所以他去了滄州。次日午後,我和覺心等出寺門散步,遠遠望見一片樹林,碧綠蔭蔭。我們一同出來的六人,就走到林子裡,因為貪涼坐得久了些,太陽都快西沉。這時正想起身回寺,只見空中灰濛濛一片,像霧一樣,又聽到嘰嘰喳喳的聲音。漸漸看到飛揚的塵土像雲一樣翻動。不久,見到無數老幼男女遍野,競相狂奔,像山崩海湧一樣衝將過來。才知道是後有兵馬追擊。一同坐在樹林裡的人,各自逃散,只有覺心和我在一起。不能再回寺裡去了。也不能走大路,就向南面慌亂跑去,一路上歇宿的多是小廟,每天只能吃一餐。
我們逢溝涉水,路錯繞道,就這樣一路走去。一天走在路上,腹內感到十分飢餓,就在樹下一個荒泵旁歇息,我對覺心說:「咱們從雲南到南方,又從南方到北京。現在又從北而南,往返二萬多里,徒勞跋涉,所立志願也沒有實現。披剃師給我起法號紹如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弘法利生。現在看來,這些都絕了緣份,真是慚愧至極啊!我法名讀體,」體「就是身,就是」法身理體「。」讀「經教才能懂得經教所闡明的」理「,理明白了,闡釋道理的文字就可以忘了。這就像借助於手指標示月亮,見了月亮就無須注意那個手指了,這是同樣的道理。現在我要把我的號改為見月。」我們二人反來覆去想啊想,越想越覺悲慼,傷心的淚水不覺卜簌簌落了下來,這時有一老人從旁經過,見我二人感傷得如此悲痛,便前來問是什麼原因。我詳細講了長途行腳而又不能實現願望之苦痛。老人連聲嘆息不已,對我們說:「我姓李,是吃長素的道人,孤獨一人沒有親眷。給人家小孩教書,因為兵馬大亂才回家來,就在前面小莊上。可以請你們前去同暫住一宿,然後再走。」到了他家一看,屋裡已被流賊搶劫一空,他就去鄰家借了些粗面,烤了餅子供我們吃。第二天我們就向他告別動身了。
又走了六天,上了南宮縣大道。至午後都沒有化齋之處,遙望遠處有一小庵。來到庵前,覺心留在外面,我獨自進去。只見一位老僧,沒有人幫他,正在自己燒火作飯。我向他合掌問訊,也不還禮。我就上去替他燒火。飯熟了,他自己盛了飯,坐在那裡吃起來。我也自己動手取了碗筷,盛了飯坐下吃起來,我也不說話。他吃一碗,我添第二碗。他才開口說:「世上從不曾見過有你這種人,主人沒開口,自己倒動手盛飯吃。」我回答說:「世上從未見到過你這種人,客人站在面前,都不說句客氣話請吃飯,所以我就自己動手。」他看著我大笑說:「倒也是個禪和子。我年少時出去參訪善知識,到處行腳,因為不老練,常常挨餓,你今天是這樣,請隨量吃吧!」我說:「門外還有一道友。」他一聽很喜歡。說:「請他進來一起吃。」我和覺心飽餐一頓,起身告別,他不肯,又留我們住了三天。
九月初,我們到了江南瓜州,於息浪庵掛單。遇到一個雲南僧,號清如。談起行腳的事,知道他在北方遭遇兵馬之難才回到南方來。第二天便和我與覺心一起渡江,前往甘露寺。當家師法號平素,也是老鄉,長期住在鎮江府,皈依信仰他的人很多。他最喜歡雲南人到江南來參學。清如先進去替我們通報,我和覺心接著進去禮拜。平素師問我們行腳遇難之事,我毫無隱諱地照實說了。平素師安慰說:「我少年時參訪,也遇到許多逆境,但求道之心絲毫沒有退墮,今天才有這點因緣。你們二人尋師求戒,往返南北,經歷了種種坎坷,最初發的願心沒有懈怠下來,以後你們教化開導眾生的因緣,自然會很殊勝。現在暫且放寬心住在這裡。開春崇禎十年元旦,是我的母難日(即母親生他的日子),要諷誦五大部經以報母恩。你們二人可以和眾僧一起誦經。衣單,我負責給你們辦理。到誦經期畢,再走不遲。」我說:「三昧和尚遙居在北京,我們不能再去,只好等他回到南方來時,再求受戒。現在我想去天童寺參禪。」平素師讚助,為我們置辦了行李外,又贈給我們每人路費銀二兩五錢。
二月初三日到達丹陽縣橋頭,想搭客船過河。覺心把行李放在腳下,只顧觀看各個船家互相排擠,爭相拉攬客人,不想被囊行李被人偷走。我們只好嘆息我們的因緣怎麼到了這種地步!幸好我的路費還揣在身上。日到中午時分,我們來到海會庵投宿,見我們沒有帶行李,不肯安單。我們告訴他行李在橋頭丟失。這個庵離橋頭不遠,他們去了解到確是實情,便送我們進了雲水堂(即接納行腳僧暫時安單之處)。遇到二位遊方僧,我們北上時曾與他們同行數日。知道我二人行腳,就說:「你們求戒,三昧和尚已經離開北京,正月在揚州府石塔寺開戒。現在他應丹徒縣海潮庵之請,二月初八日起期,你們趕快去受戒。」聽到這一消息,鬱結在心中的愁悶完全煙消雲散了。
第二天早上,我同覺心又回頭去海潮庵,恰巧遇到三昧和尚入庵。聽說教授師(即負責向新戒教授禮儀和戒律內容的僧人)是楚地人,法號熏六,心胸宏大,智慧妙巧,輔導教化很威嚴,總理戒期中一切事務。我就請求知賓師(即接待外來客人之僧人)引我到熏六師居住的寮房禮拜。師父問我鄉籍,我答:「雲南。」師說:「此庵當家師為埋葬他師父起期,每人交銀一兩,衣缽自備。」我說:「行李在丹陽丟完了。身上只有二兩三錢路費。」教授師說:「這只夠一個人攢單並造衣缽。」我又為覺心求單,接著就派人送我進了戒堂,把覺心送去行堂(作雜務者)寮。
新戒堂的引禮師(照看新來受戒僧人的起居和紀律的僧人),法號耳園,山東人,性情耿直,但缺少靈活性。見我沒有一點行李,又不請戒律讀本,終日坐在自己的單位上,不發一言,又不違犯戒堂堂規,又沒有事情去請教他,因此他心裡對我很不高興,就指斥我說:「見月,此處不是讓你坐不語禪,為什麼你不請《律讀》好好地熟讀呢?」我答:「我不識字,也沒有錢請《律讀》。」凡是進來一個求戒僧人安單,引禮師就叫我說:「見月,你到這裡坐,把單位讓給這個新來的人。」我就遵命,拿起衣缽向後面移一個單位坐下。這樣,後進堂的有十幾個人,每來一個人就讓我退讓一單位。又來了最後一人進堂,高單(即用木板搭成的連鋪大床)上已無單位了,就叫我移到地下與香燈(專管殿堂上香點燈的僧人)共坐,我毫無怨聲,只作遊戲想。同堂的眾戒兄見到這種情景,都很不平,說我懦弱至極。我說:「修行以忍辱為本,何況都是同戒,理應移讓。」
時間逐漸臨近背誦《毗尼日用》(受戒前,先須在教授師指導下學習戒律內容,預先須把戒律背熟,經過檢驗,方能登壇受戒)。引禮師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名,意思想折伏我。各位戒兄也為我著急,說:「量你也背不出來,為什麼不去拜求引禮師把名字排在後面?」我說:「到明天再看。」次日一早,引禮師拿著名簽帶引我等九人,到教授師前禮拜後,我一口氣朗聲背誦完畢,就像把瓶中水傾倒出來一樣無滯無礙。教授師說:「你每天默坐,不發一言,說不識字,今天卻背得如此純熟。」我說:「並不是我不識字,因為無錢請律書,所以默坐,專心聽左右鄰單戒兄讀誦,因此就記住了。」教授師很高興,並賜茶給我喝。回到堂裡,各位同戒都前來向我祝賀,其中和我最相投契者,有十三人,都能這樣背誦。
這一戒期讀《梵網經》。香雪闍黎師(稱戒師)代大座(即正座),四班首(首、西、後、堂)輪流復講。有一天,首座師,法號樂如,復講,他只把三昧和尚寫的《直解》念了一遍,一字不增,一字不減,未作一點解釋!我和相契合的幾位戒兄並坐在一排,相互遞著眼色,失口微笑。首座師看到,很不高興,回到堂中,就指名要我們十人復講。自來新受戒的沙彌沒有這種事情,無非是用這種變通手段,逼令我們向他懺悔。過了三天、不見一人前去求悔,他祇得把所開列的名單,呈送方丈。三昧和尚以為是實情舉薦,就一一慈允。這真是弄假成真,再難於停止下來。
到了我要復講的那天,內外人眾都驚駭一片,都來旁聽。和尚和二位師父(香雪闍黎師和熏六教授師),也在後面設座臨席,慈降加庇。所要講的內容,是《梵網經》上卷中的《十金剛種子、第十信心位》,我開卷把文句念完,先總括說了大義,然後依文作了解釋。下面聽眾,異口同聲稱讚。三昧和尚和二位師父都很欣慰。接著我去方丈室禮謝,和尚賜給我被褥衣履。熏教授師問我:「你依誰聽經?」我說:「在雲南時,依披剃師。行腳到寶慶府,遇到自如法師代顓愚大師講《楞嚴四依解》,我也曾跟隨聽講。」熏師說:「顓大師是我的依止師,自如法師是我的契友。你怎麼不早說!」熏師對我更加看重,馬上就施給覺心衣缽,讓他入堂受戒。
三月廿日午後,有個丹陽縣賀家子侄,少年書生,性情傲慢,不信三寶,醉酒入庵,直接闖進方丈室,一屁股坐在和尚法座之上,嘻笑放肆。侍者上前諫勸他反而呵斥。寺中僧眾不服,把他驅趕走了。第二天一早,這個書生邀約一夥人來庵滋擾生事。和尚馬上令圓戒罷期。平常寺中晚課多有在家居士隨喜參加。熏師想用方便辦法把這樁事平息下去,保全道場,所以在晚課完畢時,把大家召集至韋馱菩薩前,說:「今天,道場被魔撓礙搗亂,不能善始善終。你們弟子之中,有願捨身命維護法門的人,就出來擔當!」說完,大家都默然不語。我就應聲推開眾人站出來,向熏師頂禮。師說:「你只一人,怎麼能行呢?」我說:「和尚的戒弟子,遍佈天下,我一人當先,其它人都會隨之而來的。出家人無妻子可戀,無產業可系,無功名可保,無身命可惜;托缽飽餐,不帶分文;叢林棲止,不納房租。凡是僧家,以戒為親,何況為了維護法門,誰不勇敢向前!縱使用它一年二年時間,必除魔黨。請和尚和二師放心晏安,不必以此為念。如果那一夥人中,果然有捨得妻子產業,能放棄功名、身命的人,讓他站出來與我較量一番。否則,各家把自己的學業做好,好自培養自身道德之本。自古以來,有了德行和好文章,庠中士子都能成就功名,應當作天下大丈夫。難道有誰願意為別人的是非,而喪盡自己的德行!」熏師說:「你今天在眾人中作了這樣的承諾,以後一定要依言而行,還怕什麼法門不淨,魔障不除!」眾人散去,參加晚課的人都聽到了,這話就輾轉傳播開去。
第二天午後,果然有二十多人,都是庠中齋長和鄉中父老,來到庵上拜見熏教師,也把我請去了,雙方以理講和。圓戒時間未改,仍在四月八日。和尚召集大家來方丈室,對二位師父以及久隨身邊的上座說:「今天道場魔事如果不起,就顯不出見月。你們為佛法,為人師,應當像他一樣有膽量有心行。我在這個傳戒期裡,總算找得人才了。」大家聽後,禮謝而退。二位師父開導指示我們同戒十三人,今後就作和尚身邊的隨侍,希望我們今後成為法門樑棟。
初十日回揚州石塔寺。楊州府慧照寺禮請和尚,擇期於四月二十日開戒。五月初八日是三昧和尚大壽,我們同戒都沒有禮物可送。我提議說:「可以裱一長卷,自己畫上五十三參圖奉獻和尚祝壽,因此我就沒有時間,不能隨大家去慧照寺起期開戒了。」和尚聽說之後,就叫我進方丈室去靜心作畫,並笑著說:「見月啊,你初登戒品,就入我室。」我慚愧地向和尚拜謝。六月二十日,海道鄭公,請和尚在石塔寺建盂蘭盆會,講《孝衡鈔》。和尚就命我去慧照寺,代香雪闍黎師座,講《梵網經直解》,並請香雪師回石塔寺代和尚座,講《孝衡鈔》。兩處道場都在七月十日圓滿。
香師開示我和同戒們,去求和尚更改各自原有的法名,以便常隨和尚任事。各位同戒依言,前往方丈室,都爭先禮拜求和尚賜法名,只有我一人退到後面,頂禮和尚,跪地白告說:「我因披剃師指示,才得發心離開雲南,南來向和尚乞受大戒。若無披剃師,我就不能削髮出家,也不能受具足戒而成為真正的僧人。懇請和尚大慈允聽,讓我仍叫舊名,使我不忘根本,我願終身常侍和尚座前。」和尚說:「我當年初受戒後,諸位上座也勸我求律祖更換法名。想來,律祖諱如字,我是寂字,披剃師諱海字,我也不敢忘本,把姓字改了,超越海字。我弘戒律三十多年,今天見到你的存心與我相同,這是不自欺心啊!作善知識,所依重的就是行德,不在於叫什麼法名。我允許你仍稱原來的名字。」
那時泰興縣毗尼庵請和尚於八月十五日開戒,大家都隨行。熏教授師於初十日晚,向和尚白告,請定各堂執事,說:「我現在教授新戒,中氣不足,精神漸弱,應該設置一名教誡西堂。總理各堂戒事,其單位安在新戒的首堂。這項任務,只有見月可以擔當,請和尚智鑒裁度。」和尚馬上命侍者召集兩序僧眾(寺中僧人,在方丈之下分東西兩班序列,稱兩序;東序負責寺中之行政管理;西序負責法務管理)來方丈室,向眾人宣告對我的委派。我跪地白告說:「我今年四月八日才圓受具足戒,還不到半年,哪裡敢擔負這樣的重任。我自己都沒諳熟律法而再去教人,擔心不利於新戒,也辜負了和尚的慈恩。請和尚在各位上座中,另選能擔當此任者委任吧!」和尚說:「熏教授推薦得不錯。我也知道你的心行作用。十地菩薩尚且還要寄位修行(到人間擔負一定的工作,以利修行)。你今天不妨一邊自學,一邊教誨他人,以體諒我的用心。這樣就一舉兩利。」兩序人眾齊聲說:「你應當隨順和尚慈令,不可以再推辭了。」我只好拜受了這項差委。
我同戒中的映字、蒼悟為這次戒期的書記,慧生、以仁、裕如、若愚、觀之等為引禮。人人發奮努力,嚴肅認真,和尚座下還未曾有過像海潮庵同期受戒的這一批人那麼熱情鼎盛,其首堂引禮師(即總理全部行禮職事的僧人),就是我受戒時的引禮師耳園,我雖然居於掌權之位,但動止都以師禮尊讓他。他也不執我相(很謙虛),一切堂規之定奪,都謙讓照我的意思行事。但我的內心一直懷著慚愧,倘若遇到樂於學習戒律的人前來請教,我怎麼做才能讓他辨明是非,而高興滿意呢?一天晚上,我前去拜詣熏師寮,向他說明了我的擔心。師說:「三藏中有大小乘律一千多卷,我沒有閱讀過。你既然有此志向,可以請來邊讀邊學,將來作大律師,才不辜負我在廣眾之中把你識別出來。」因此就找了人前往嘉興,請了一部《廣律》回來。從此,白天我料理各堂戒規,夜裡則挑燈展卷,詳詳細細閱讀學習。一旦遇到文字上古老意義上難懂之處,苦於沒有精通的人請教,只有掩卷長嘆。這時我唯有向菩薩禮拜祈禱,乞求加被開曉。每次禮罷,少坐片刻,再展卷體會其義,就會如開門見山,豁然無疑了。像這樣的不思議感應,每次都如此。
這一期傳戒法會,定於十一月五日圓滿。結期前三日,本堂新受戒的弟子們,念我教誨不倦之心,共同製作了一件黃綢大衣(僧袍)送我,我對他們說:「和尚與教授師,把重任委付給我,理應盡心盡職,為輔助弘化法門出力,難道是為了邀名貪惠方作首領不成!」我嚴肅謝絕。他們捧著衣服去到方丈室拜跪,向和尚陳述了奉供此衣之因由。和尚對我說:「戒律之中只禁貪求,不禁自願佈施。你可以受取。」我說:「在下不受此衣有兩重意思:其一,我自愧於戒行淺而責任重,恐有不足的地方,有人借此產生譭謗;其二,和尚法門高峻,唯恐以後擔任各項職事的人以此為肇端,開了先例,所以不受。」和尚讚同了我的想法,對各新戒說:「西堂不受此衣,為的是保全己德,惜護法門。你們不要再強送了!」
十月八日隨和尚返回揚州石塔寺。高郵縣承天寺,禮請和尚十二月初一日起期傳戒,至開春正月十五日圓滿,我仍擔任西堂之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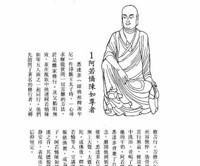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