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悟前與悟後,從事相看並無甚區別。人人鼻直眼橫,個個吃飯打眠。悟者在日常生活中與未悟者一模一樣,如《金剛經》云:「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就連佛陀亦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們一樣,每日過著托缽游化的生涯。但如來著衣時通身放光,持缽時手上放光,次第乞食時眼中放光,入城洗足時足下放光,乞食吃飯時口中放光,乃至敷座而坐時大地震動也。正因為如來不著四相,不住六塵故,便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之所以六根門頭放光動地者,如來一舉一動全是實相般若的現覺妙用,即觀照般若也。悟與未悟者之間的區別,就看在同樣的日常生活中有實相般若的觀照妙用現覺與否。生活中若有實相般若的觀照妙用現覺,則頭頭是道,法法皆妙。若無,則處處執著,事事磕絆。所以參禪以明心見性為其終極目的,為的是悟後起修,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悟後的光景是要將阿賴耶識中的一切種子和盤托出,此時「根、塵、識」三之妄念全轉變為佛性。親見本來面目後,從本體上看是一理平等的,無佛與眾生之別,亦無眾生成佛之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菩提煩惱,同是空花」。未悟前,一切皆假,全是意識卜度之所支配,好比戴著有色眼鏡看物一般;悟後,則一切皆真,全是真心之所流露,猶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天台「佛即頌」云:「從來皆是妄,今日妄皆真;但複本時性,更無一法新!」悟前不減一法,悟後亦不增一法。可謂「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也。蘇東坡悟道偈云:「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歸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所以悟後的光景亦無奇特處,平常平常。肚饑三碗粥,口幹一杯茶。
平等不外差別,差別不外平等。就平等中看其差別,悟後的光景悉皆隨順時節因緣而度日。牛頭宗的口頭禪是「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山河大地是如來,木頭碌碡盡菩提。嬉笑瞋怒,真心妙用;瞬目揚眉,佛法宣流。蓋依體起用,攝用歸體,「一切法皆是佛法」。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為用之體,用為體之用。以體用從來不二故,則始終左右逢源,無不自得。悟前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恁麼也不得;悟後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也得。因為悟後不起思量卜度意識,所以一切總得自在。《華嚴經》說:「佛法即世間法,世間法即佛法。」《壇經》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尋兔角!」以故不能以佛法分別世間法,亦不能以世間法分別佛法。以「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故,世間法即是佛法;以「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故,佛法即是世間法。悟後者正因為知此道理,故不起思量分別意識,能隨順時節因緣而過。正如《圓覺經》云:
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善男子: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彼諸眾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為「隨順覺性」。善男子:汝等當知,如是眾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及大菩薩,植眾德本。佛說是人,名為「成就一切種智」。
這段經文對參禪來說十分重要,只要學人識得平等理體,就自然不會在遇境隨緣時隨波逐浪,自當截斷眾流也。而「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這幾句話,是參禪的無上寶鑒。要做到這幾句話,必須是悟後之人。那悟後的光景,乃信手拈來無不是也。不妨舉幾則近代禪者的悟後光景如下,聊以塞責。
一、印光大師的深信因果與儉以養德
近代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他盡畢生心血力弘淨土法門,極倡「因果輪迴」之說,以挽頹風、輔綱紀。他認為欲拯救國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護國息災,非提倡因果報應不可。大師對因果的深信實令人心悅誠服,游有維所著《印光大師言行錄》云:「師見‘楊歧燈盞明千古,寶壽生薑辣萬年’之聯語,並《沙彌律》中盜用常住之戒,心甚凜凜。及在蓮華寺司庫房,凡整理糖食,手黏及氣味者,唯用紙揩,不敢以舌餂。蓋誠敬篤實,慎因畏果,師之賦性然也。」對此事,大師亦曾自述:「至湖北蓮花寺,討一最苦之行單(打煤炭,燒四十多人之開水,日夜不斷。水須自挑,煤渣亦須自挑出。以尚未受戒,能令住,已算慈悲了)。次年四月,副寺回去。庫頭有病,和尚見光誠實,令照應庫房。銀錢帳算,和尚自了。光初出家,見‘楊歧燈盞明千古,寶壽生薑辣萬年’之對,並《沙彌律》言‘盜用常住財物之報’,心甚凜凜。凡整理糖食,手有粘及氣味者,均不敢用口舌餂食,但以紙揩而已。」連粘在手上的剩糖殘粒都不敢用舌頭舔,生怕內心起貪念。可見大師對戒律的嚴淨已從「制身不犯」達到「制心不起」的地步了,欲從惡止善行而達到心性的明淨。他傚法的是「楊岐燈盞,寶壽生薑」精神,楊岐用燈公私分明,寶壽監寺不以常住生薑買方丈人情,這種佳話當然值得千古傳頌。印光大師對此二則典故還夾著云:
楊岐燈盞者,楊岐方會禪師在石霜圓會下作監院。夜間看經,自己另買油,不將常住油私用。
寶壽生薑者,洞山誌寶禪師(寶壽乃其別號)在五祖師戒禪師會下作監院。五祖戒有寒病,當用生薑紅糖熬膏,以備常服。侍者往庫房求此二物,監院曰:「常住公物,何可私用?拏錢來買!」戒禪師即令持錢去買,且深契其人。後,洞山住持缺人,有求戒禪師舉所知者。戒云:「買生薑漢可以。」
印光大師不但自己深信因果,而且還倡印民間一切善書以提倡因果報應之說,更為極力批駁宋明理學排斥因果的偏見。印光大師在生活方面亦極為節儉,一生只蓋過一床棉被,一雙棉鞋都穿了三十餘年,展轉從浙江普陀山帶到了蘇州靈岩山。或有信眾供養營養補品等,自己一概不食用,差人送往寧波觀宗寺供養諦閑法師,認為自己福報不夠,消受不起名貴補品。以故他一生極為勤勞、惜福、深信因果、老實念佛。在蘇州靈岩山寺的印公紀念室裡,珍藏著大師生前用過的一塊手錶與一件毛巾被,那算是大師生前用過的最為奢侈的東西了。
印老亦極為慈悲,愛惜物命,洗手的淨盆都是有蓋子的,以防蚊蟲落水而溺死。他佛前的油燈也是有燈罩的,以防飛蛾撲火而喪生。後來,他移錫蘇州靈岩山寺,他的這種作風影響了後世的靈岩山寺僧眾,至今靈岩山寺佛前的油燈都是套燈罩的。
大師素有「飯後一勺開水」的機鋒垂示,及「你有多麼大的福氣?竟如此糟蹋」的棒喝警策。宿植善根者,無不於大師極乎尋常而又極乎峻烈的機鋒棒喝下,心生慚愧,低頭認錯,痛悔前非,爭作如來所稱讚的「能悔健兒」也。弘一律師曾在《略述印光大師盛德》一文中說:「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無菜。師自云:‘初至普陀時,晨食有鹹菜,因北方人吃不慣,故改為僅食白粥,已三十餘年矣。’食畢,以舌舐碗,至極淨為止。復以開水注入碗中,滌蕩其餘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嚥下,惟恐輕棄殘餘之飯粒也。至午食時,飯一碗,大眾菜一碗。師食之,飯菜盡盡。先以舌舐碗,又注入開水滌蕩以漱口,與晨食無異。」弘一律師當年就於此「飯後一勺開水」的垂示中,便能識取大師機鋒。崇尚印光大師儉以養德的高尚節操,以俾自己亦力躬實踐之,終於成為了世人所敬仰的一代佛門律師。
文中又說:「師自行如是,而勸人亦極其嚴厲。見有客人食後,碗內剩飯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麼大的福氣?竟如此糟蹋!’」並且「此事常常有,餘屢聞及人言之。」可見,印光大師的當頭棒喝是沒有任何時間界限的,亦是不論身份地位高下的,一律平等。凡有揮霍奢侈之習者,無不吃此大師的當頭一棒,就連當時民國政府的林森主席也都沒有放過。據說,林森主席當年謁見大師時,因用齋不小心掉兩粒米飯於餐桌上,被大師看見了,就毫不客氣地呵斥道:「汝有多大的福氣,竟如此糟蹋糧食!」林森主席聞聽此言,猶晴空一聲巨雷響,震耳欲聾,面帶羞慚,連忙撿起桌上所剩殘粒於嘴中嚥下。這便成了今日倡導「儉以養德」良風的佳話。
事實上,印光大師「飯後一勺開水」的垂示,早已影響了蘇州靈岩山寺的全體僧眾,那裡的僧人在自己的一日三餐中,都有「飯後一勺開水」注入碗中,滌蕩碗邊剩餘湯汁的習慣。這不僅鑄造了愛惜糧食的素養,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偉大的僧格。
在人們物質生活水準日益提高的今天,在擺闊氣、講排場的佳餚盛宴前,過度的揮霍奢侈、鋪張浪費之糜風仍舊盛行。故於此時,重溫印光大師當年的這番公案,不覺催人淚下,倍感親切!我們雖未親嘗大師當年的機鋒棒喝,但若能把大師的「飯後一勺開水」的垂示,付諸於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話,便能力挽奢侈狂瀾於此時,競倡節儉良風於未來。要知道,深信因果與儉以養德,實乃大師悟後之光景。據大師給高鶴年居士信中所言「誰知宿業,竟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而論,大師約莫於五十八歲前就徹悟了,因為此信復於民國八年(1919)夏曆十二月初四日,而大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1961)夏曆十一月初四日。
二、諦閑法師的智慧與慈悲
近代中興天台的諦閑法師,與印光大師是真蓮友,一生不離講席半步,「教演天台,行修淨土」。他曾在二十八歲,講《法華經》至「舍利弗授記品」 時,儼然入定一小時多,出定後舌燦蓮花,從此辯才無礙。寶靜法師所輯《諦公大師年譜》載:「師二十八歲,光緒十一年(1885),復至龍華聽大海法師講《楞嚴》。又講偏座,圓經後,諸同學又堅邀至杭州六通寺開大座,講《法華》。一日,講至‘舍利弗授記品’,寂然入定,默不一言,約一小時之久。眾咸嘆為希有。繼而出定,辯才無礙。答難析疑,如瓶瀉千里。雲疊萬重,卷舒自在。莫之能御也。」他早年也與南京毗盧寺的印魁法師一道去參謁過赤山的法忍老人,深受啟發。晚年重興寧波觀宗講寺,創觀宗學社,造弘法僧才。據倓虛法師的回憶,諦老的智慧無邊,慈悲亦無邊。
曾有一位在鎮江金山江天禪寺禪堂曾任香燈之職的老實僧,在六月初六曬藏經之日,有個小沙彌調侃他說:「香燈師:今天大家都忙著搬藏經曬,你為什麼不把蠟燭也拿出來曬曬呢?否則會被蟲子蛀了的。」那老實巴結的香燈師就信以為真,竟把滿滿一籮筐蠟燭搬到火辣辣的太陽底下去曬了。午後收拾蠟燭時,蠟油留了一地,用鏟子鏟了一下午。待晚上大眾進堂坐香時,香燈師怎麼也點不著蠟燭,維那看不耐煩了,叫他換一支好的點,換了又換,依舊點不著。有人說:「不用換了,全是蠟芯兒了,換了也點不著,好好的蠟燭全被他曬成蠟芯兒了。」維那走進一看,全剩下滿滿的一籮筐蠟芯兒,沒一支能點著的蠟燭了。維那下逐客令說: 「你這麼有智慧的人,在這裡當香燈有點屈才了,你應該去諦閑法師那裡學教去呀,學好了就可以混飯(弘范)三界了,待你登座說法時,我就給你呼鐘聲偈,不妨今晚就起單前去吧!」大眾見維那已下逐客令了,也就沒說情挽留。那香燈師二話沒說,就連夜兼程了。
數日後,抵諦老那裡去學教。他在客堂掛單時,就把金山維那的原話和盤托出了,人家一聽就知道是個癡人。按常理,是不能留這樣的人學教的。但因諦老幾日前曾責罵客堂里人不留人學教故,客堂里人便把這個人就帶去難為諦閑了,以酬前日責罵之恨。諦閑一聽那僧之言,雖知是個愚癡人,但因有言在先,凡來寺學教者須留單故,便將錯就錯地將其留下常住了。
諦老十分慈悲,先令其入大寮(廚房)行堂掃地,以培植福祉。那僧便言聽計從,行堂掃地三年,任勞任怨,一絲不苟。諦閑見其老誠,便教其先背誦《楞嚴經》。豈料那僧以三年時間,竟將洋洋七萬餘言的《楞嚴經》倒背如流了。諦老知其是個法器,又教他背誦《法華經》,並授習《法華會義》。開悟的《楞嚴》,成佛的《法華》,那僧背誦這二部經典有功德,不料竟開智慧了。通過九年的修福修慧,竟能代諦老講經說法了。但每次講經前,迎請法師登堂入室陞座時,都要維那打引磬到齋堂門前去迎請,因為他不捨行堂掃地之福。
後來,金山維那帶了一批人去諦老那裡參座聽經。正好那天諦閑不能分身,便由那僧代座開講。又維那身體不適,便由金山維那代呼鐘聲偈。那個金山維那呼鐘聲偈畢,不料抬頭一看,座上講經的卻正是當年在金山曬蠟的那個香燈師,真是出人意料,金山維那當下頓生慚愧,這不外乎是給他當頭一棒也。但這位法師,在跟隨諦老至南京毗盧寺講經期中,竟撒手西歸了。諦老甚捨不得,哭得極為悲傷。這位法師,後人竟不知道他的法名字號,而以「曬蠟法師」這個綽號而代稱之。
諦老能把一個在太陽底下曬蠟燭的木訥癡僧,竟然教化成了一代講經法師。這正顯示了諦閑的慈悲與智慧非比尋常,這豈不是諦閑的悟後光景乎!
三、弘一律師的「咸也好,淡也好」
持律行者弘一法師,他幼年時就特別喜歡養貓,懂得愛惜物命,出家後更如是。他曾在上海豐子愷家暫住了幾日,每次要坐藤椅前都要先將藤椅左右搖晃幾下。後經豐君的詢問才知,原來弘老是為了避免傷害藤椅夾縫中的微細昆蟲,故在坐之前先打個招呼,好讓小生命搬家逃生。弘老並且在臨終前都囑咐隨身侍者妙蓮法師說,他歿後,其木龕之四個木腳下須用四個碗墊著,並且碗裡須斟滿水,以防火化時有傷害生靈之命。弘老愛惜物命的慈悲,亦是他人無法比肩的。他「以華嚴為教理,以戒律為行持,以淨土為果證」,獨享生活之藝術,更有禪者之風範。
在弘老眼裡,一切皆好,弗往非華嚴大解脫境界。夏丏尊曾請他去白馬湖小住了一段日子,早上起來便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去洗面。夏氏看了,忍不住地說:「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弘老卻道:「那裡!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夏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弘老過午不食,早餐午飯由夏家負責送去,每天只要一碗飯一碗菜。一次,有個朋友送了四樣菜去齋他,夏也在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的,夏嘗了口說:「這太鹹了!」弘老卻說:「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又一次,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去齋他,夏也在席。其中有一碗淡得非常的,夏說:「這太淡了!」
弘老卻說:「好的!淡的也有淡的滋味,也好的!」弘老不論吃什麼飯菜,都能吃得津津有味,滿腔歡喜。夏丏尊在《生活的藝術》中描述弘老吃飯的神情說:「碗裡所有的原料只是些萊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劃入口裡,鄭重地用筷夾起一塊萊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夏還說:「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蓆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夏丏尊與弘一法師是摯友,夏對弘老獨享生活的藝術境界作評曰: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當我見他吃萊菔白菜時那種愉稅丁寧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為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裡,也不限在畫裡,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作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他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為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囫圇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著衣,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憮然!
總之,弘一律師的「咸也好,淡也好」,的確是悟後的光景。正因為他以華嚴為境界,故在他眼裡一切總是好的,沒有不好的東西。在禪者的智慧眼中,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
四、能海上師的剃頭慈悲
極力修習密宗之能海上師,他從西藏學密歸來後,大弘黃教於山西五台山、浙江三門、上海等處。在上海金剛道場時,據他的學生道安法師說,上師每次剃頭時不許頭髮落地,須使頭髮全落在膝蓋前鋪好的報紙上。剃好頭後,則用報紙把頭髮包起來塞在瓦當裡或牆縫裡。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防止頭髮落地捅傷昆蟲而已。
能海上師的剃頭慈悲,亦頗有禪者風範,亦是悟後之光景。既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那麼蚊蟲螞蟻亦不例外,悉皆有成佛之望。以故佛陀制不殺戒,廣勸一切行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也。我人修學佛法,亦須從「戒殺食素」做起。宗門教人參「狗子有佛性也無」的話頭,豈不令人深思也哉?
五、本煥長老的「看破放下,隨緣自在」
剛往生不久的本煥長老,一生復興叢林幾處。但他每到一處叢林做方丈,當任期滿後他都主動退居讓賢,或轉錫別處去復興另一座叢林。即便是他晚年著手創建的弘法寺,亦是在年近百歲高齡時退居潛修。這點甚具紫柏、憨山之灑脫宗風,亦說明本老是一位能看破放下一切名聞利養,隨緣自在的禪者。功成身退,隨緣行化。
記得有一次,弘法佛學院全體師生前去聆聽老和尚開示。他說:「你們都是大和尚,而我雖然一百零五歲了,但我現在什麼事都不能做了,所以我是個百歲小和尚。整日只會吃飯吃粥,放下手來卻空空如也。說空空如也,並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有的是煩惱,有的是業障。所以我每天念佛,懺悔業障。」本老從「空」 邊說自己年事已高,再不能領眾修行,住持日常院務工作了,所以退居閑寮。唯有「萬緣看破,通身放下」的禪者,才能有如此灑脫的胸襟。本老又從「有」邊說自己有的是煩惱業障,所以在吃粥吃飯的同時還須勤念彌陀。這正是隨緣自在的一面。寥寥數語,則將「空有不二」之般若中道義和盤托出了也。
本老在一百零四歲壽誕上說:「有人稱我為‘佛門泰斗’,全中國就這一個。也有人講‘哎呀!本煥有多了不起’!其實沒什麼了不起!我還是一個小和尚,還是一個四歲的小男孩。我不能把自己放得太高,‘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嘛!」他慨嘆年輕人妄想特重說:「你們年輕人妄想多,想了還要做,做了以後還要成!什麼都想要,怎麼可能放得下?」他為令行人能徹底放下心頭煩惱故,則慈悲開示道:「用功時,有一點要記住,切切不能有執著,宗門向來是‘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切都要斬得乾乾淨淨,什麼也不可得,哪怕有一絲一毫的掛念都不行。」這分明是握一把金剛王寶劍,令人直下像「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也。他又怕行人落空解而不務實修,故說:「發道心,是要你自己發,不是要我發,得到好處是你自己的,不是我的。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誰也不能代替你。」
本老始終本空、有圓融不二之道,說「空」,則令人看破一切,放下萬緣,一念不生;此時方具備念佛參禪的先決條件。談「有」,則令人真為生死,發菩提心,隨緣念佛,得大自在。空則遣相去執,有則念佛參禪。所以說「看破放下,隨緣自在」是本老的悟後光景,本地風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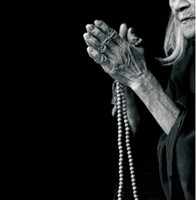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淨慧法師
淨慧法師 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道證法師
道證法師 蕅益大師
蕅益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星雲法師
星雲法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