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思量不思量
有一次,藥山惟儼禪師正在禪坐的時候,來了一位行腳的出家人,看到靜坐中的禪師就問:「你在這裡孤坐不動,思量一些什麼事情啊!」
「思量不思量。」禪師回答說。
「既然是不思量,又如何思量呢?」這位行腳僧不放鬆地追問。
「非思量。」禪師針鋒相對地回答。
這則公案從一般的理論上看,既思量,卻又不思量,似乎互為矛盾,其實有它的道理,意思是說:禪雖然不是文字知解,主張言語道斷,但是通過文字知解,可以把握不可言處的真髓,也唯有超越知識見解上的執著,才能探驪得珠,體會真正的禪味。
22 佛法無二般
韓愈韓文公因諫迎佛骨表,被貶潮州,因當地文化落後,無人論學談心,不得已,有一次去參訪大顛寶通禪師,問道:「禪師春秋多少?」
寶通禪師提起手中念珠道:「會嗎?」
韓愈答道:「不會!」
寶通補充一句:「晝夜一百八。」
韓愈仍不知其意,因為無法對談,不得不回去,後來越想越放不下,為什麼一個和尚的對話,自己會聽不懂?第二天再來時,在門前碰到首座,便請示首座,昨天與寶通禪師之對話,意旨如何?
首座聽完後,便扣齒三下,韓愈更是茫然不解。
韓愈到法堂內見到寶通禪師,再重問道:「禪師春秋多少?」
寶通禪師亦扣齒三下。
韓愈忽然像明白了什麼,說道:「原來佛法無二般。」
寶通禪師問道:「為什麼呢?」
韓愈答道:「剛才首座的回答,也跟禪師一樣。」
寶通禪師像自語似的道:「佛儒之道無二般,我和你也是一樣!」
韓愈終於有省,後皈依大顛禪師,執弟子禮。
韓愈問春秋多少,其實人生歲月何用掛心,要緊的是人天合一,心佛不二,所謂道的大統,儒也佛也,一以貫之也。是故禪師以手珠示意,佛儒一統也,及晝夜一百八,意指歲月無多,莫為佛儒爭論,佛道儒道,共襄攜手可也。
23 見與不見
佛監禪師聽完學僧守珣禪師的見地後,道:「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
接著又舉靈雲禪師的詩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靈雲的不疑之處?」
守珣立刻回道:「莫道靈云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
佛監又問:「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任’,哪裡是他未徹處?」
守珣恭謹地道:「深知禪師老婆心切。」
說完便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漫始抬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佛監禪師認為守珣悟了,但圓悟禪師不以為然,想再勘察一下守珣禪師的見地,就與他遊山,在一潭邊,忽然將守珣禪師推入水中,問道:「牛頭法融未見四祖時如何?」
守珣:「潭深魚聚。」
圓悟:「見後如何?」
守珣:「樹高招風。」
圓悟:「見與未見時如何?」
守珣:「伸腳在縮腳裡。」
圓悟禪師聽後大為讀嘆,認為守珣真的悟了。
禪者有沒有覺悟?這是可以經過考試得知的,「行家面前一開口,便知有沒有」,悟與不悟,禪師一勘便知。守珣禪師的悟道,一考又再考,總要見出真章才能通過。
24 不許為師
兜率從悅禪師,參訪密行的清素禪師,非常禮敬,有一次因食荔枝,經過清素禪師的窗口就很恭敬地說道:「長老!這是家鄉江西來的水果,請你吃幾個!」
清素很歡喜的接過荔枝,感慨的說道:「自從先師圓寂後,不得此食已久了。」
從悅問道:「長老先師是何大德?」
清素答道:「慈明禪師,我在他座下忝為職事一十三年。」
從悅禪師非常驚訝讚歎道:「十三年堪忍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說後,便將手上的荔枝全部供養給清素長老。
清素即以感激的態度說道:「我因福薄,先師授記,不許傳人,今看你如此虔誠,為此荔枝之緣,竟違先師之記,將你的心得告訴我!」
從悅禪師具道所見。
清素開示道:「世界是佛魔共有的,最後放下時,要能入佛,不能入魔。」
從悅禪師得到印可以後,清素禪師教誡:「我今為你點破,讓你得大自在,但切不可說是承嗣我的!真淨克文才是你的老師。」
「要學佛道,先結人緣」,荔枝有緣,即能悟道。「佛法在恭敬中求」,從悅對前輩的恭敬,恭敬中就能得道。古人一飯之思,終生不忘,如清素禪師,一荔之賜,竟肯道破心眼,此乃感恩有緣也。「不可嗣我,當可嗣真淨克文禪師」,師資相助相信,亦禪門之美談也。
25 也是恁麼
法慶禪師的侍者因讀了《洞山錄》這本禪書以後,感慨的說道:「古人在生死中那麼任性,實在好奇怪!」
法慶禪師因而答道:「我坐化時,你可用話喚醒我,若叫得回來,亦即生死自在之士,奇怪,也不奇怪。」
侍者看看禪師,禪師作預言頌云:「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揚卻,免佔檀那地土。」
時光迅速,到了五月初五,禪師就將所有的衣物交給侍者供僧結緣,剛聽到初夜的鐘聲,就跌坐圓寂,脈搏停止,呼吸全無,侍者記取當時的談話,就喚道:「禪師!禪師!」
許久,法慶睜開眼睛,問道:「做什麼?」
侍者:「禪師為什麼不將衣帽鞋襪穿好而去?」
法慶:「當初來時,我根本就不曾帶什麼呀!」
侍者一定要將衣服給法慶禪師穿上。
法慶:「一點都不肯留給後人。」
侍者:「正恁麼時如何?」
法慶:「也只恁麼。」並又寫了一偈:「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足+孛)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
說完儼然而化。
若有人問:「禪者有生死沒有?」
答曰:「禪者或有生死,但禪者在生死中非常自在耳。」赤裸裸的來,赤裸裸的去面對生死,而能從容放下,正恁麼時,亦即是解脫自由了。
26 將軍的懺悔
夢窗國師有一次搭船渡河,當船正要開航離岸時,有位帶著佩刀拿著鞭子的將軍,大喊道:「等一下,船夫!載我過去!」
全船的人都說道:「船已開行,不可回頭。」
船夫也大聲回答道:「請等一下班吧!」
這時,夢窗國師說道:「船家,船離岸未多遠,給他方便,回頭載他吧!」
船夫看到是一位出家師父講話,因此就把船開回頭讓那位將軍上船。將軍上船以後,剛好站在夢窗國師的身邊,拿起鞭子就抽打了夢窗國師一下,嘴裡還罵道:「和尚!走開點,把座位讓給我!」
這一鞭打在夢窗國師頭上,鮮紅的血汨汨地流下,國師不發一言就把位子讓出,大家看了都非常害怕,不敢大聲講話,都竊竊私語,說禪師要船載他,他還打他。將軍已知道剛才的情況,但仍不好意思認錯。
船到對岸,夢窗國師跟著大家下船,走到水邊默默地、靜靜地把臉上的血洗掉,這位蠻橫的將軍終於覺得對不起夢窗國師,上前跪在水邊對國師懺悔道:「禪師,對不起!」
夢窗國師心平氣和地說:「不要緊,出外的人心情總是不太好。」
世間上什麼力量最大?忍辱的力量最大。佛說:「修道的人不能忍受譭謗、惡罵、譏諷如飲甘露者,不名為有力大人」。世間上的拳頭刀槍,使人畏懼,不能服人,唯有忍辱才能感化頑強。諸葛亮七擒孟獲,廉頗向藺相如負荊請罪,此皆忍辱所化也。
27 一切現成
浙江的法眼文益禪師,往閩南參訪時,行腳途中遇雪,就暫在地藏院中借住,因為風雪多日,與院主桂琛禪師相談甚契,雪停後,文益辭別桂琛禪師,擬繼續行腳。桂琛想送法眼一程,兩人走到山門外時,桂琛禪師指著路邊一塊大石頭問道:「大德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不知道這一塊石頭在你心內或心外?」
法眼文益毫不考慮的回答道:「依唯識學講,心外無法,當然是在心內。」
桂琛禪師抓住了話柄,就問道:「你不是在行腳雲遊嗎?為什麼要放一塊石頭在心內?」
法眼文益瞠目結舌,不知回答,因此就決定留下來解開這個謎團。法眼在地藏院中的歲月,每天都向桂琛禪師呈上自己的見解,但桂琛禪師總認為法眼的見解不夠透徹,有一天,桂琛禪師就對他說道:「佛法不是這樣子的!」
法眼不得已,再從另一個角度報告自己的心得,桂琛禪師仍然否定說:「佛法不是這樣子的!」
法眼經過多次呈報,均不蒙桂琛印可,只得嘆道:「我已經詞窮意盡了。」
桂琛禪師聽後,補充一句道:「若論佛法一切現成!」
在這句言下,法眼文益禪師大悟,後開法眼宗,門徒千餘,得法者八十三人。
在佛法裡,所謂馬上長角,頭上安頭,總是多餘的事;「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是多美妙的境界。吾人心上負擔豈止一塊石頭,所謂金錢、名位、愛情、生活等,已經壓得喘不過氣,還有那是非、得失、榮辱、苦樂等,更是奇重無比。如果明白一切現成,何用勞煩於唯心與唯識?
28 生死由他
後唐保福禪師將要辭世示寂時,向大眾說道:「我近來氣力不繼,我想大概世緣時限已快到了。」
門徒弟子們聽後,紛紛說道:「師父法體仍很健康」,「弟子們仍需師父指導」,「要求師父常住世間為眾生說法」,種種議論不一。
其中有一位弟子問道:「時限若已到時,禪師是去好呢?還是留住好?」
保福禪師用非常安詳的風度,非常親切的口吻反問道:「你說是怎麼樣才好呢?」
這個弟子毫不考慮的答道:「生也好,死也好,一切隨緣任它去好了。」
禪師哈哈一笑說道:「我心裡要講的話,不知什麼時候都被你偷聽去了。」
言訖跏趺示寂。
說到生死,在一般世人看來,生之可喜,死之可悲,但在悟道者的眼中,生固非可喜,死亦非可悲。生死是一體兩面,生死循環,本是自然之理。不少禪者都說生死兩者與他們都不相干。如宗衍禪師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滴,漚生漚滅,復歸於水。」道楷禪師示寂時更說得好:「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禪者生死,有先祭而滅,有坐立而亡,有入水唱歌而去,有上山掘地自埋。總之,生不貪求,死不畏懼,禪者視生死均為解脫也。
29 宜默不宜喧
靈樹院有一年夏安居的時候,五代時的後漢劉王堅持禮請雲門禪師及其寺內大眾全體到王宮內過夏。諸位法師在宮內接受宮女們禮敬問法,鶯鶯燕燕,熱鬧非凡。尤其劉王虔誠重法,故禪修講座,無日無之。寺中耆宿也都樂於向宮女和太監們說法。但唯有云門禪師一人卻在一旁默默坐禪,致使宮女們都不敢親近請示。
有一位值殿的官員,經常看到這種情形,就向雲門禪師請示法要,雲門禪師總是一默,值殿官員不但不以為忤,反而更加尊敬,就在碧玉殿前貼一首詩道:「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卻禪門總不言。」
禪門高僧,一向如閑雲野鶴,或居山林,或住水邊,三衣一具,隨緣任運,即使法緣殊勝,王宮侯第,亦不為利誘,不為權動。如雲門禪師者,「一默一聲雷」,雖不言語,實則有如雷轟頂之開示,吾人如在沉默時體會出千言萬語,就可以說已透到一點禪的消息了。
30 堂中首座
靈樹如敏禪師的靈樹院,二十年來都沒有人負責「首座」之職,每當人家問起,禪師就回答:「我的首座剛剛出生啊!」又有人問,即答:「我的首座正在牧牛啊!」再有人問,即答:「我的首座正在行腳之中。」等語回答,便問的人都不知所故。
有一天禪師忽然命令大眾撞鐘擊鼓,並吩咐至山門迎接首座。正在寺眾們訝異中,雲門禪師飄然而至,如敏禪師便請其擔任首座之職。
於是大家都相傳著靈樹禪師有能知過去和未來的神通。
不久,五代後漢劉晟,將興兵征討時,聞靈樹禪師神通,便親自入院,擬請示禪師一些未知的將來,以便在決策問題上參考。
哪裡知靈樹禪師已預知其意,就事先示寂,劉王到達時,就非常生氣的道:「禪師是生的什麼病?怎麼這麼快就圓寂呢?」
侍者非常誠實的回答道:「禪師並沒有生病,他早知道你要來,所以就先示寂了,但留有一個盒子要給你。」
劉王接過盒子一看,內有紙條一張,上面寫著「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劉王悟其意旨,遂就罷兵,禮請雲門禪師晉住靈樹院,擔任住持。
古德,很少濫竽充數,有的虛其位,以待其人;有的雖學德俱全,但也要以待有緣,龍天推出。一寺首座,一待多年,可見選擇人才的慎事。雲門禪師初在靈樹院,後至雲門山,興教利眾,靈樹如敏禪師早就預見,但是亦要待大器晚成也。
31 化緣度眾
昭引和尚雲水各地,被大家認做是一個行腳僧時,有信徒來請示:「發脾氣要如何改呢?」
「脾氣皆由瞋心而來,這樣好了,我來跟你化緣,你把脾氣和瞋心給我好嗎?」
信徒的兒子非常貪睡,父母不知如何改變他,昭引和尚就到他家,把夢中的兒子搖醒:「我來化緣你的睡覺,你把睡覺給我吧!」聽到信徒夫妻吵架,他就去化緣吵架。信徒喝酒他就去化緣喝酒。
昭引和尚畢生皆以化緣度眾,凡是他人的陋習,均是以化緣改之,所到之處蒙其感化的信眾不計其數。
化緣有緣,這本是美好的事啊!
32 無事手
唐朝相國裴休,是一位學禪的居士,他將其參禪的心得,用文字記載下來,並編印成冊,冊成之後,非常恭敬地呈送到黃檗禪師面前,希望禪師對其內容有所指示。
黃檗禪師接過手後,看也不看的就往桌上一放,許久才問裴休宰相道:「你懂我的意思嗎?」
裴休誠實的回答:「不懂!」
黃檗禪師方便開示道:「『禪』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你把佛法表示在筆墨文字上,是扼殺了佛法的真義,也失去吾宗的宗旨,故我才不看。」
裴休聽後,對禪更加契入,也更加對黃檗禪師敬重,並作頌讚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
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示何人?」
黃檗禪師看了這頌,並無說好說壞之意,只道:
「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只揖等閑人。」
黃檗禪師在中國禪宗史裡,是一位最坦蕩耿直的人,他和臨濟禪師,成為棒喝的始祖。六十五歲時,住江西龍興寺,裴休將他的說法輯為《傳法心要》上卷,七十二歲,在河南開元寺,裴休為他的開示輯為《傳法心要》下卷,但他對裴休的記錄,竟然看也不看,可見其禪門高風,不易一見了。
33 怎能會得
雲門禪師在睦州陳尊宿那裡開悟以後,就出外遊方。在江州遇到官員陳操尚書,陳尚書亦禪門學者,初見面時便帶著考試的口氣問道:「什麼才是衲僧的行腳事?」
雲門不答,反問道:「你這話問過幾個人了?」
尚書:「不管我問過幾個人,我今天只問你。」
雲門:「這事且慢談,我先問你,什麼是如來一代三藏教義?」
尚書:「黃卷赤軸。」
雲門:「這只是文字紙墨,不是佛法真義,請再說,什麼是教義?」
尚書:「口欲言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
雲門:「口欲言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尚未說對,請再說,什麼是教義?」
陳尚書無言回答。
雲門:「據說尚書平時研讀《法華經》?」
尚書:「是!」
雲門:「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請問,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
尚書茫然不知所對。
雲門:「十經五論看過的師僧,拋卻經論後再入叢林修行,經過十年二十年也不見得就會開悟,尚書只看幾卷經論怎能會得?」
尚書:「請禪師原諒,是我罪過!」
從此雲門住陳尚書家宅三年。
禪門證悟,不怕不開口,只要一開口,就知有沒有。禪者不是逞口舌之能,任意一說,雲門初參睦州,被他三搥其胸,三逐門外,後來千辛萬苦,才能開悟,故陳尚書幾部經論,怎能相比呢?
34 啐啄妙用
河南寶應院的南院慧顒禪師,是臨濟禪師的門下,有一次示眾道:「現在各禪林間對於啐啄之機的問題(喻時機成熟契悟之義)僅具有啐啄同時的體而已,尚未具有啐啄同時的妙用。」
有一位學僧向前問道:「請問什麼是啐啄同時的妙用?」
慧顒禪師解釋道:「啐啄是像擊石出火、閃電出光,間不容髮的時機所作的。如果有意識地去做時便失其機了。」
學僧不滿意的抗辯道:「對此我尚有疑問。」
慧顒禪師慈悲的道:「什麼疑問?」
學僧輕慢地大聲道:「已經不是疑問,是你說的更教人糊塗了。」
慧顒禪師聽後,便對此學僧用棒打了過去。學僧正要開口辯解,慧顒禪師就將他趕出山門。
這個學僧後來在雲門禪師座下參學,一日,就將其離開慧顒禪師處的情形告訴文偃禪師的門人聽,門人聽後問道:「慧顒禪師棒打你,此棒有所折斷嗎?」
學僧聽後,豁然有悟,便趕快回到南院,想向慧顒禪師懺悔,但慧顒禪師已經遷化圓寂,南院寶應寺已由風穴延沼禪師擔任住持。
風穴延沼禪師問道:「你當時是想怎樣才不服先師的?」
學僧回道:「我當時好像是在燈影搖晃中走路一樣。」
風穴探問了究竟後,說道:「那麼你已經會了,我給你印證。」
有語云:「飯未煮熟,不要隨便一開;蛋未孵熟,不要妄自一啄。」啐啄妙用,當下一刻,即是一個新的生命,慧顒的打逐,只是孵化期中,文偃門人的一句「棒有折斷嗎?」這才是一啄的妙用!
35 不得不說
道怤禪師是溫州永義人氏,有一次去參訪雪峰義存禪師,初見面時,雪峰禪師就問道:「你是什麼地方人氏?」
道怤回答道:「溫州。」
「那麼你和一宿覺(玄覺永嘉禪師,因參訪六祖惠能大師,留住一宿,故名一宿覺)是同鄉了。」
道怤不知玄覺和他同是溫州永嘉人,所以不解,故再問道:「一宿覺是什麼地方的人啊?」
雪峰禪師認為道怤孤陋寡聞,就責備道:「好!好!應該要打你一頓棒,今天且放過你。」
有一天雪峰禪師,集合大眾開堂說法:「堂堂密密地。」
雪峰禪師只此一句話,就靜默不再說下去,一山大眾均不會其意。
道怤走出大眾,問道:「什麼是堂堂密密地?」
雪峰禪師責備道:「你講什麼?」
道怤恭謹肅立。
雪峰禪師等大眾無語,又再說道:「向上宗乘事,堂堂密密地。」
道怤聽後,立刻長跪,舉手抱拳說道:「道怤自來本山已經數年,還沒有聽過禪師這樣的慈悲示誨。」
「向來雖然沒有這樣說過,今天已經說出來了,是不是對你有所妨礙呢?」
「不敢,禪師是不得已說的。」
「不,這是你使我不得不說的」。
從此師資契入,雪峰禪師座下,又多一個禪人。
36 高僧真儀
裴休相國有一次到龍興寺時,看見壁畫問道:「這是什麼圖相?」
寺僧:「是高僧的真儀。」
裴休:「真儀我是看到了,可是高僧呢?」
寺僧無言以對。
裴休:「不知此地有否禪人?」
寺僧:「最近有位來掛單的雲水僧,好像是一位禪僧。」
裴休便勞寺僧請此雲水僧出來相見。
裴休:「剛剛我向寺僧請示的問題,不知可否請你開示?」
雲水僧:「請相公發問。」
裴休正開口要問時,雲水僧高叫一聲:「相公!」
裴休隨聲應諾。
雲水僧:「在什麼處?」
裴休當下如獲寶珠,說道:「原來你就是高僧。」
隨即拜此雲水僧為師。
此雲水僧不是別人,正是黃檗希運禪師。
裴休宰相真是奉行了黃檗希運禪師說的「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當作如是求!」原來真儀是真儀,高僧是高僧!
37 佛堂無佛
陝西地方汾州無業禪師,初參馬祖道一禪師時,由於相貌魁偉,聲如洪鐘,馬祖一見即取笑他道:「巍巍佛堂,其中無佛!」
無業隨即作禮,恭敬地說道:「三乘文學,自信粗窮其旨;但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
馬祖見來意真誠,就開示道:「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了即是悟;迷即眾生,悟即是佛。」
無業:「心佛眾生外,更有佛法否?」
馬祖:「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豈別有佛法?如手作業,拳空如手。」
無業:「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馬祖:「祖師今何在,且去別時來!」
無業禪師不得已,就告辭出門,馬祖隨即叫一聲:「大德!」
無業禪師迴首。
馬祖:「是什麼?」
當下無業禪師跪下禮拜,哭訴道:「本謂佛道長遠,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
馬祖:「這個鈍漢悟了也!」
說起修行,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佛道?說遠,須三大阿僧祇劫;說近,當下即是。如懷璉禪師云:「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吾人心外求法,妄失自己,才勞動諸佛祖師,千說萬說,才知回頭。馬祖一聲,無業迴首,本來面目,當下認識。「魚在水中休覓水,日行山嶺莫尋山。」你說鈍漢,可是了悟了也。
38 覆船生死
有位學僧去參拜雪峰禪師,雪峰禪師問他道:「從哪裡來?」
學僧回答道:「我從覆船禪師那邊來。」
雪峰禪師故意幽他一默:「生死之海還沒有渡回去,你為什麼先要覆船呢?」
這個學僧不了解雪峰禪師的意思,便回去把經過告訴覆船禪師。覆船禪師對這個學僧說道:「你真愚笨,為什麼不說我已超越生死苦海所以才覆船呢?」
於是這位學僧又回到雪峰禪師的地方來,雪峰禪師又問道:「既已覆船,還來做什麼?」
學僧胸有成竹的說道:「因為既已超越生死,還不覆船做什麼?」
雪峰聽後,就不客氣的說道:「這句話是你老師教的,不是你說的,我這裡有二十棒請你轉給你的老師覆船,告訴他,另外還有二十棒,就留給我自己吃──這一切與你無關。」
雪峰禪師給覆船和尚二十棒,自己也甘願挨二十棒,這個公案至為明顯:禪,應該無言說教,所謂言語道斷,不應在語言上傳來傳去,兩個人都賣弄了禪,所以各挨二十棒!這不關學僧的事,學僧還不夠資格挨二十棒哩!
39 得意忘言
洞山禪師走到(水+防)潭的時候,看到一個職僧對大家說法,他不引經據典,只聽他自言自語的道:「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
洞山禪師聽後,走上前便問道:「我不問佛界和道界,只問剛才在這裡說佛界道界的是什麼人?」
那位說法的人,在本寺是一位很重要的職事,是一位首座大師,人們叫他初首座。
初首座聽後,默然不作一語。
可是洞山禪師不饒過他,一直追問道:「為什麼不快說呢?」
初首座不甘示,弱答道:「快了就無所得。」
洞山不以為然,反駁道:「你說都沒說,還談什麼快了就無所得?」
初首座又默然。
洞山禪師這才覺得遇到了對手,因此就溫和說道:「佛和道都只是名詞而已,我問你的,你為什麼不引證教義來說呢?」
初首座好像遇到好的機會,迫不及待的問道:「教義是怎麼說的?」
洞山禪師拍掌大笑回答道:」得意忘言!「
禪者與禪者對話時名為機鋒,有時聽起來,不知兩人說些什麼,好像牛頭不對馬嘴,但當事者彼此,實有至理在焉。如洞山禪師要他快說,初首座沉默以對,初首座反問他怎麼說,他說」得意忘言「,實則忘言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禪啊!
40 答禪非問
有一位禪師寫了兩句話要弟子們參究,那兩句話是:「綿綿陰雨二人行,怎奈天不淋一人。」
弟子們得到這個話題便議論了起來。
第一個說:「兩個人走在雨地裡,有一個人卻不淋雨,那是因為他穿了雨衣。」
第二個說:「那是一個局部的陣雨,有時候連馬背上都是一邊淋雨,另一邊是乾的,兩個人走在雨地裡,有一個人不淋雨,卻是乾的,那有什麼稀奇。」
第三個弟子得意的說:「你們都說錯了,明明是綿綿細雨嘛,怎可說是局部陣雨,那是一定有一個人走在屋簷底下。」
這樣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好像都有理,都沒有個完。
最後,禪師看時機已到,就對大家揭開謎底道:「你們都執著於‘不淋一人’的話題,且也執著得過份厲害,那當然爭論不休。由於爭論,所以距離真理越來越遠。其實啊,所謂‘不淋一人’,不就是兩人都在淋雨嗎?」
所以,要談禪,不要從問的方面回答,要從不問的方面去體會。禪門語錄數千卷,看起來都是問答式的教學。其實,有時間的並不要回答,回答的也不是要問的。問答有爭論,自悟無爭論,問答不是猜謎語,在回答之外,還有這個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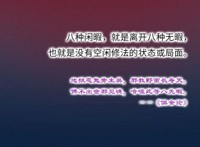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淨界法師
淨界法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宏海法師
宏海法師 來果老和尚
來果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紹雲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 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夢參法師
夢參法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