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蓮老和尚(1922-2008.6.25),祖籍安徽省巢縣,九歲出家,二十歲(1941年)時至南京大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受戒之後於印光祖師的道場蘇州靈岩山寺參學,1949年,法師前往香江,隨即掩關於大嶼山及青山,專修凡20年。妙蓮法師20年閉關修持,解行並重,期間修持多達10次的「般舟三昧」。修持一次「般舟三昧」,歷時90天,其中常行,不坐不臥,24小時中皆在經行念佛、繞佛或拜佛,無有間斷,每天除一次中餐外,完全將身心投入念佛中,非一般常人所能及。
環境愈苦道愈堅
俗語說「多難興邦」,如果生活安適,人心就很容易怠惰、腐化,這也是經驗之談。還有說「茅簷之下有將相,幾多白屋出公卿」,貧寒人家的兒女,在困苦中奮鬥出來,這些孩子才有用;富貴人家的子弟多半嬌生慣養,很容易不長進,當然這也是依事實而說。
我們修道也是如此,環境愈苦、生活愈苦,道心就愈堅強;一切都講舒適、處處都講自在,那也是好容易懈怠。想想看!我們本師釋迦世尊為什麼不在皇宮裡修道,皇宮裡修道多麼自在,還要跑到凍死人的雪山去幹什麼?虛雲老和尚初出家時住在山洞中,山洞裡潮濕沒有陽光,有的是毒蛇、老虎及種種野獸。冬天冰天雪地的,非常寒冷;夏天又是三、四十度的熱,睡覺時汗還是流個不停,我們家鄉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有福報,要好好地珍惜、用功,不要把大好日子空過了,尤其要有個積極了生死之念。有福報當然是好,但不要被這福迷昏了!那就難怪我們佛家講,學佛的人千萬不能求生天。想想看!享人間富貴都迷了,生到天上享那個微妙的五欲,怎麼得了!大家好好依佛言、依古祖善知識之話,一心看破放下,念佛求生西方,這些話千萬要記住!
憶昔初到香港時
這次是為了紀念我1949年農曆十月初一在香港閉關而打的佛七。今年是1988年,香港閉關到現在已經三十九年了,只是打七做個紀念,我並沒有想到什麼,但是有幾位發心的菩薩,今天買了包子、壽桃、壽面來供佛供僧,祝福閉關的紀念,並要我說說當時閉關的情形,那我就略略地告訴諸位。
記得1949年二月,我從大陸靈岩山寺下來,經上海、杭州,再到江西、湖南,然後沿著粵漢鐵路到廣東,四月初八特別到廣東南華寺拜見虛雲老和尚,那時虛雲老和尚正在傳最後一次的三壇大戒。在廣東停留半個月,四月尾到香港,在香港過端午,那年是閏六月,前一個六月上大嶼山寶蓮寺掛單。
那時候到香港,好多的青年僧被時代的浪潮所淘汰,當時我就是一個鐵打的心性:「佛法在,我在;佛法不在,我也在!縱然把佛法毀滅了、把我的僧服脫了也好,我的心穿了如來的智慧衣,這是脫不了的!沒辦法消滅我心中如來的信仰,你的思想打不進我的心內。」
香港雖然沒有大廟,在小廟掛個單還是可以的。可是我們修道的人,並不是有了食住就好,應該要學要修,那時候修學的心非常之強,很想要用功,但要住在能用功的地方才可以,有飯吃沒得用功的地方也不能住。常時古祖交代學人:你到了那個地方吃得好、睡得好,若不能修道就要趕快跑;如果那個地方吃不好、睡不好,但能修道、能弘法,你就勉勵自己多住一些時候。
你想我們在大陸受過叢林生活的嚴格訓練,一到了香港,雖然還是在廟裡掛單,但那個沒有叢林規則的環境那是我們所能受的?尤其我當時正是二十八歲的青年,正是那樣高如泰山的心,總是想深入經藏、想修證念佛三昧,可是當時生活、存身隨時都在不測中,還有什麼時間給你來研究經教、修行拜佛?
不過人愈是在困苦之年,愈能發道心;愈是在苦難之中,生死心愈切。我那時就想要閉關:「不管啦!晚上死也好、明天死也好,只要有一口氣在,趕快要看經、拜佛。」從蘇州靈岩山寺下來,修道的心確乎堅固,總算諸佛菩薩加被,在香港有了閉關的因緣。
艱苦閉關二十載
大嶼山所有的佛教徒在山上大概有一百多間茅蓬,小的茅蓬可住一兩個,大的茅蓬有住十幾個的;寶蓮寺算是大茅蓬,也是十方的道場,所以我們在那裡掛單。到大嶼山還沒一個月,同參都知道有一位妙蓮法師,那時候大家都是青年法師,山上那些人好像同我特別有緣,大家都對我好。
我看到那個情形,而且山上的茅蓬這麼多,要找個關房並不成問題,所以我頭一天說出想閉關的意願,第二天就有一個了。當然,那時候也沒講究什麼空氣啦、陽光啦、安適啦,沒有的!只要有間關房能安身、能修行用功,有一頓飯吃就好了,因此十月初一就在法華淨苑正式閉關。
我那關房多麼大呢?約兩公尺寬、三公尺長的一間小茅蓬,人站在中間,兩手一伸就碰到兩邊的牆,一拜佛下去,後面就頂到壁,就是這麼一點大。那房子靠著西北角的山壁,是個冬不見陽光、夏不透風的地方--冬天陽光照不進來,要陽光沒有陽光;到了夏天陽光是有,但要風沒有風。那時有位從大陸一起到香港的法師來看我,他說:「哎呀!你在這種地方閉關,別說住三年,要我三天也住不住!」
關房裡地濕,上面又滴水,每年從臘月起,一直到六月,水都是從天花板一滴滴的朝下滴,桌上的釘子都爛了,你看那種的濕氣!所以第二年起就患風濕,在關房中患了一年多的風濕病,一直以念「阿彌陀佛」來抗疼,慢慢的也就好了。但我現在這個腿還是腫的,還有這個咳痰,都是住那關房受的病。這就是修行的因緣不具足,道業未成,身體就受病了。就像一顆種子下在陽光不充足、空氣不流通的地方,自然也就長不好。
那樣困苦的環境我怎麼能住得下去?就是心沉定下來,心沒有還想要到上海、南京,或南北那裡的,連關房外面都不要出來。心沉定下來、靜下來才能住得住;如果不靜下來,再好的關房也住不住。所以想閉關的人那麼多,但有的人閉個三、五個月就跑出來了。閉關不是那麼簡單的,要受一番苦。
閉關那時候日中一食,早上就是三片餅乾加個熱開水,中午吃的哪有像我們現在這樣的好菜?吃飯就是吃飯,菜就是一樣菜。在三、四十年前,台灣的生活還不是一樣的苦,現在才豐衣足食的這樣好。
這一閉關就是六年,六年後為什麼要出來?因為茅蓬破了,連玻璃都沒有了!香港大嶼山的風就好像台灣花蓮、恆春的風那麼大,本來就是舊房子,經過五、六年,大風一掃又漏水,再住身體受不了,沒辦法就出關,另外找關房。從大嶼山下來,經過四、五年才在青山找到關房--也就是佛慈精舍,在那裡一住就是十四年;青山那關房也是舊房子,住十四年又壞了,前後兩次共閉關了二十年。
關內修般舟三昧
在關房裡,我發願修十次「般舟三昧」。修般舟三昧的歷程,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都是繞行念阿彌陀佛,禮佛是可以,但不能坐也不能臥,要經過九十天才算功德圓滿。這是一種最精進的念佛法,也是對治昏沉、散亂最好的方法。經行的方式是在水泥地上赤腳繞佛,在念法上或快或慢,隨意的,當時就念我自己獨創的六度佛,前五句有聲表前五度,第六句無聲表般若度。
當我修般舟三昧一期九十天中,我的腳一直都是腫的,雖然腫但還可以忍痛,所以能支持到底。在初修的幾天,一天中總會有一個多小時在半昏迷狀態,另一個多小時處在全昏迷中,但心裡還是有點明白。昏迷盡管昏迷,人還是照樣在走圈子、心還是在念佛,因關房小常常頭碰到牆,但也能藉此清醒。
初開始的幾天,一天之中大約會跌倒一次,然後在地上知覺全失的睡了兩三分鐘。醒來以後雖又立刻再走,但內心覺得十分悔愧:「修般舟三昧應該不眠不休的,我今天跌倒了,這就是修持的願力不夠,所以沒有達到修此法的標準。」
每當修到苦得很難忍受時,我就想:「每個人都有死,軍人戰死在沙場、學士死在文壇、公務員死在其赴公之時,都是死得其所。我是出家人,如果因為修般舟三昧而死在佛堂,也是死得其所,有何遺憾呢?死既不怕,又何患於修持走圈時不能忍受?況且修行如逆水行舟、推石上山,在這過程中,稍一鬆懈,功夫即會一落千丈,所以不能稍懈我志。」每每以此自勉,更一心一意地每天念佛十萬聲,就這樣在艱苦中度過九十天。
其實要求感應,就是要捨自己一個色身,要拚命!古來高僧大德哪個不是從苦中磨煉過來的?就說慈雲懺主吧!他在修般舟三昧的時候,兩條腿都是腫的。腫了是不是就休息呢?休息就前功盡棄了!他的腿腫了不理它,還是經行用功,到腫得皮裂開了也不理它,裂開了流血,血流止了流黃水,還是不理它,以死自誓!
要顧著這個色身,道業還能成就嗎?身體瘦得只剩下皮包著骨、包著筋,累得倒下來,倒下來還沒死,還有口氣在,他仍是照常行道。到這時候觀世音菩薩感應了,朝他口裡灌甘露,一灌甘露,不但他身體好了,智慧也來了,也有了福德因緣。
古祖大德就是這樣苦修啊!要是照凡夫情見來想,打般舟七晝夜九十天都那麼經行,那不是要辛苦死了?其實不會辛苦的,辛苦就做不到。經行時行不在行,好像腳不沾地,愈行愈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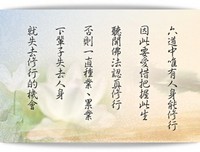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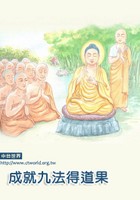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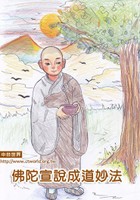





 印光大師
印光大師 玄奘大師
玄奘大師 大安法師
大安法師 如瑞法師
如瑞法師 慧律法師
慧律法師 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 省庵大師
省庵大師 界詮法師
界詮法師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 妙蓮老和尚
妙蓮老和尚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 蓮池大師
蓮池大師 其他法師
其他法師 憨山大師
憨山大師 廣欽老和尚
廣欽老和尚 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